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知青一代的精神史。以大眼界诊断时代,以大悲悯直指人心,具有社会广角与人性深度的心灵书写。
灵动的言表与深刻的思辨自然融合,当代文学的独步标高之作。
内容简介
《日夜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精品。作品通过几位五○后从知青年代到转型时期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和时代的变迁。作品的聚焦点是性格、情感及价值观的冲突,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后知青”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艺术家、流亡者等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用他们各自的一生回答了时代的精神之问。《日夜书》是知青一代的精神史。以大眼界诊断时代,以大悲悯直指人心,具有社会广角与人性深度的心灵书写。灵动的言表与深刻的思辨自然融合,当代文学的独步标高之作。
作者简介
韩少功,男,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曾任海南省作协主席(1996年)、海南省文联主席(2000年)等职。主要作品有“韩少功作品系列”十卷(上海文艺版)曾获多种奖项:《西望茅草地》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飞过蓝天》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马桥词典》获上海市第四届中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奖长篇小说一等奖(1998年)、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2010年);《暗示》获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2002年);《山南水北》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2007年);《赶马的老三》获首届萧红文学奖(2011年);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勋章(2002年)。作品有三十多种外文译本在境外出版。精彩书评
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陈思和
像是畸人录,又像是英雄传,对历史和现实具有很强的概括力。
——格非
整整一代人的安魂曲。
——欧阳江河
目录
01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作者附注
精彩书摘
01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走,使我相信人的性格几乎同指纹一样难以改变。当年我与他同居一室,同挤一床,实在不是一件太爽的事。他从无叠被子的习惯,甚至没洗脚就钻被窝,弄得床上泥沙哗啦啦地丰富。这都不说了。早上被队长的哨音惊醒,忙乱之下,同室者的农具总是被他顺手牵羊,帽子、裤子、衬衣也说不定到了他的身上。用蚊帐擦脸,在裤裆里掏袜子,此类举动也在所难免。好在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像样的行头,穿乱了也就乱了,抓错了也就错了,不都是几件破东西么,共产主义就是不分你我的乱来。
我穿上一件红背心,发现衣角有“公用”二字。其实不是“公用”,是“大甲”的艺术体和圆章形:“大”字一圆就像“公”,“甲”字一圆就像“用”。这种醒目的联署双章,几乎盖满他的一切用品,显然是一位老母的良苦用心所在--怕他丢三拉四,也怕他错认了人家的衣物,所以才到处下针,标注物主,主张物权。
这位老母肯定没想到,再多的盖章加封在白马湖茶场依然无效,字体艺术纯属弄巧成拙,倒使物权保护成了物权开放:大家一致认定那两个字就是“公用”,只能这样认,必须这么认,怎么看也应该这样认。大家从此心安理得。
大甲看见我身上的红背心,觉得“公用”二字颇为眼熟,但看看自己身上不知来处的衣物,也没法吭声了。
他只是讨厌别人叫他“公用哥”或“公用佬”或“公用鳖”,似乎“公用”只能与公共厕所一类相联系,充其量只能派给虾兵蟹将一类角色。用他的话来说,他是艺术家,即便眼下公子落难,将来拨云见日,见到总统都可以眼睛向上翻的。你不信吗?你怎么不承认事实呢?你脑子里进了臭大粪吧?他眼下就可以用小提琴拉出柴可夫斯基,可以拉扯脖子跳出维吾尔族舞蹈,还可以憋住嗓门在浴室里唱出鼻窦共鸣,放在哪个艺术院团都是前途无量。何况他吃奶时就开始创作,夹尿布时就有灵感,油画、水彩画、钢笔画、雕塑等等都是无师自通和出手不凡,就算用臭烘烘的脚丫子来画,也比那些学院派老家伙不知要强多少。这样的大人物,怎么能被你们“公用”?
每个土砖房都住五六个人,每间房里都是农民与知青混搭。农民们不相信他的天才,从他的蓬头垢面也看不出贵人面相,于是他的说服工作变得十分艰难。他得启发,得比划,得举例,得找证人,得赌咒发誓,得一次次耐心地从头再来,从而让那些农民明白“下巴琴(小提琴)”是怎么回事。更重要的,他得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艺术比猪仔和红薯更重要、更伟大、更珍贵,为什么画册上拉(斐尔)家的、达(芬奇)家的、米(开朗基罗)“家的,比县上的王主任要有用得多。
实在说不通时,他不得不辅以拳头:有个农家后生冲着他做鬼脸,一直坚信王主任能批来化肥和救灾款,相比之下你那些画算个屁呵。这个”屁“字让大甲一时无话可说,上前去一个”大背包“,把对方狠狠摔在地上,哎哟哎哟直叫唤。
“真是没文化。”大甲抹一抹头发,大概有黄钟毁弃的悲愤,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找干部告状去了。
“你不吹牛会病吗?”
“你不吹牛会死吗?
“你自己不好好干活,还妨碍人家,存心破坏呵?”
“姚大甲,你还敢打人,街痞子,暴脑壳,日本鬼子、地主恶霸呵?”
……
这就是吴场长后来常有的责骂。场长一气之下还煽来耳光,没料到大甲居然还手,闹出一场恶拼。
场领导后来议了几次,最后决定单独划一块地给大甲,算是画地为牢,隔离防疫,把他当成了大肠杆菌。
出工的队伍里少了他,真是少了油盐,日子过得平淡乏味。工地上没人唱歌,没人跳舞,没人摔跤,没人吹牛皮,没人闹哄哄的赌饭票,于是锄头和粪桶似乎都沉重了不少,日影也移动得特别慢。“那个呆伙计呢?”有人会冷不防脱口而出,于是大家同生一丝遗憾,四处张望,放目寻找,直到投注对面山上一粒小小的人影。嘿,那肯定是他。那单干户也太舒服了吧?要改造也得在群众监督下改造,怎么能一个人享清福?就是,我们要声讨他,他也听不到。我们要揭发他,他耳朵不在这里呵。
大家谴责干部们的荒唐,对那家伙的特殊待遇深为不满。快看,他又走了。快看,他又坐下了。快看,他又睡下了,今天一上午就歇过好几回……那家伙大概也在张望这一边,不时送来几嗓子快意的长啸,声音飘飘忽忽地滑过山谷,落在小木桥的溪水边。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独来独往和自由自在,享受一份特许的轻松。至于他的单干任务,基本上交给了附近一伙农家娃,让他们热火朝天地代工。他的回报不过是在纸片上涂鸦,给孩子们画画坦克、飞机、老虎、古代将军什么的,给孩子的妈妈们画画牡丹、荷莲、嫦娥、观音菩萨什么的。他设计的刺绣图案,还赢得了大嫂们满心崇拜,换来了糯米粑。
他很快画名远播,连附近一些村干部也来茶场交涉,以换工的方式,换他去村里制作墙上的领袖画像和语录牌,把他奉为宣传大师,完成政治任务的救星,总是用好鱼好肉加以款待。县里文化馆还下乡求贤,让他去参与什么县城的庆典筹备,一去就两三个月。关于剧团女演员们争相给他洗鞋袜的事,关于县招待所食堂里的肉汤任他大碗喝的事,都是他这时候吹上的。
肯定是发现他这一段脸上见肉了,额头上见油了,吴场长咬牙切齿地说:“他能把蒋介石的毛鸟鸟割下来?”
旁人吓了一跳,“恐怕不行吧?”
“就是么,一个盗窃犯,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还是要把他关起来!”
旁人又吓了一跳,“他偷东西了?”
场长不回答。
“是不是偷……人?”
场长走了,扔回来一句:“迟偷早偷都是偷。”
我们没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法印证场长的高瞻远瞩。我们也没等到共产主义,同样没法印证场长有关吃饭不收饭票、餐餐有酱油、人人当地主、家家有套鞋的美好预言。我们只是等来了日复一日的困乏,等来了脚上的伤口、眼里的红丝、蚊虫的狂咬、大清早令人心惊肉跳的哨音。
不过,疲惫岁月里仍有激情涌动。坊间的传说是:有一位知青从不用左手干活,哪怕这位独臂人的工分少了一大截。他私下的解释是:如果他的左手伤了,指头不敏感了,国际小提琴帕格尼尼大奖就拿不到了呵。这种疯话足以让人吓一跳。另一则传说是,一位知青听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不去参加庆祝,反而跑到屋后的竹林里大哭一场。他后来的解释也神经兮兮:人家抢在他前面把这件事做了呵,占了先机,夺了头功,他的科研计划就全打乱啦。
大甲只是个初中留级生,不至于牛成这样。他的科学知识够得上冲天炮,够不上人造卫星。但这并不妨碍他也是美梦翩翩,曾谱写一部《伟大的姚大甲畅想曲》,咣咣咣咣,嘣嘣嘣嘣,总谱配器十分复杂,铿锵铜管和清脆竖琴一起上阵,又有快板又有慢板,又有三拍又有四拍,又有独唱又有齐唱,把自己的未来百般讴歌了一番。
当时他已离开茶场,去了附近一个生产大队--那里的书记姓胡,是个软心肠,见这一个城里娃老是被隔离,觉得他既没偷猪也没偷牛,既没有偷米也没有偷棉,凭什么把他当大肠杆菌严防死守?既然对上了眼,这位老汉二话不说,要他把行李打成包,扛上肩,跟着走,大有庇护政治难民的一腔正义。这样,大甲从此成了胡家一口子,不明不白的家庭成员,干什么都有老劳模罩着。后来,他玩到哪里就吃住在哪里,又成了梁家一口子,华家一口子,被更多的大叔大伯罩着。农忙时节,我们忙得两头不见天。他倒好,鞋袜齐整,歪戴一顶纸帽,在田野里拉一路小提琴来慰问我们,如同英国王子亲临印度难民营。“呵,在那西去列车的窗口,在那九曲黄河的上游……”他的激情朗诵分明是要气死我们。
我们躺在小溪边,遥望血色夕阳,顺着他的提琴声梦入未来。我们争相立下大誓,将来一定要狠狠地一口气吃上十个肉馅包子,要狠狠地一口气连看五场电影,要在最繁华的中山路或五一路狠狠走上八个来回……未来的好事太多,我们用各种幻想来给青春岁月镇痛。
多少年后,我再次经过这条小溪,踏上当年的小木桥,听河水仍在哗哗流响,看纷乱的茅草封掩路面,不能不想起当年。大甲早已回到城市,进过剧团,办过画展,打过群架,开过小工厂,差一点投资煤矿,又移居国外多年……但到底干了些什么,不是特别的清楚。凭一点道听途说,我知道他最终还是在艺术圈出没,在北京著名的798或宋庄这些地方混过,折腾一些“装置”和“行为”,包括什么老门系列、拓片系列、幼婴系列,以及不久前那个又有窗、又有门、还安装了复杂电光装置的青花大瓷罐……据他说,这是准备一举收拾威尼斯国际双年展的原子弹。
看来世界已经大变,我在日新月异的艺术之下已是一个老土,在青花大瓷罐面前只有可疑的兴奋,差不多就是装模作样。我左瞧右看,咳了七八声,把下巴毫无意义地揉了又揉,说眼下的艺术越来越像技术,画家都成了工程师了。
“对,说对了,这正是我追求的方向。”他指定我的鼻子。
“你的意思是,艺术就应当成为技术?”
“对,你真是个聪明人。你彻底忘掉画笔,多想想切割机和龙门吊,就可以到美术学院当教授了。”
他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当然也更不明白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不就是三岁扎小辫、五岁穿花裤、九岁还吃奶的那个留级生么?当年邻居的大婶奶汁高产,憋得自己难受,常招手叫他过去,让他扑入温暖怀抱咕嘟咕嘟吮上一番。想想看,一个家伙有了漫长的哺乳史,还能走出自己的童年?他后来走南闯北东奔西窜,但他的喉结、胡须、皱纹、宽肩膀,差不多是一个孩子的伪装,是他混迹于成人堆里的生理夸张。只有从这一点出发,你才可能理解他为何追捕盗贼时一马当先,翻山越岭,穷追不舍,直到自己被毒蜂蜇得大叫--其实他不是珍爱集体林木,只是觉得抓贼好玩。你也才可能理解他为何一转眼就去偷窃队上的橘子,为了对付守园人,又是潜伏,又是迂回,又是佯攻,又是学猫叫,直到自己失足在粪坑里--其实他对橘子并无兴趣,只是觉得做贼好玩。一切都是玩,如此而已。
对于他来说,抓贼与做贼都可能high(兴奋),也都可能不high。只有high才是硬道理。艺术不过是可以偶尔high一下的把戏。拜托,千万不要同他谈什么思想内涵、艺术风格、技法革新以及各种主义,更不要听他有口无心地胡扯这个斯基或那个列夫。他要扯,让他扯吧。他做的那个大瓷罐,可以装酸菜也可以装饲料,雇工数人耗时一年的大制作,在我看来不过是他咕嘟咕嘟喝足奶水以后,再次趴在地上,撅起屁股,捣腾一堆河沙,准备做一个魔宫。
他肯定把今天的家庭作业给忘记了,把回家吃饭给忘了。
他有家吗?我曾要来他的电子邮箱,但那信箱如同黑洞,从未出现过回复;也曾要来他的手机号,但每次打过去都遭遇关机。我只知道他大概还活在人世,偶尔在我面前冷不防地冒出来,挠挠头皮,眨眨眼睛,找点剩饭充塞自己的肚皮,然后东扯西拉一通,然后落下他的手机,揣走我的遥控器,再次消失在永无定准的旅途。最近的一段吹嘘是有关他如何解救小安子,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熟人。他说他在美国开上越野车,挎上了美式M16,带上一位黑哥们,去毒贩子们那里嘎嘎嘎(他的冲锋枪总是在叙述中发出唐老鸭的叫声)--他朝天一个点射,“fuck--Shit--”那些来自墨西哥的小杂种便统统抱着头,面向墙壁,矮下了。
“你这不是拍电影?”我说。
“你不信?那你去问小安子,你现在就打电话!”
“她怎么会在那里?”
“刚到美国,乱走乱跑,不听我的教导呵。”
“她不是在新西兰么?”
“新西兰的黑社会哪够她玩?”
一个警匪大片就这样丢下了,一段人们不必全信也不必深究的闲扯。他就是这样的一缕风,一只卡通化的公共传说,一个多动和快速的流浪汉,一个没法问候也没法告别的隐形人。他不仅没有恒定住址,从本质上说,大概还难以承担任何成年人的身份:丈夫、父亲、同事、公民、教师、纳税者、合同甲方、意见领袖、法人代表、股权所有人等。也许,这样的伪成年人,不过是把每一个城市都当积木,把每一节列车都当浪桥,把每一个窗口都当哈哈镜,要把这一辈子做成乐园。
在将来的某一天,他可能勋业辉煌名震全球,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也可能一贫如洗流落街头,像他前妻和儿子说的那样。但不管落入哪种境地,他都可能挂一支破吉它,到处弹奏自己的伟大畅想。
“公用鳖!”
“公用鳖!”
……
我从街头孩子们的叫喊中猛醒了过来。
02
我醒了过来,再次醒过来了,发现很多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我得防止自己像一个梦呓者那样把事情说乱。当时白马湖茶场有八千多亩旱土,分别划给了四个工区共八个队。在缺少金属机械和柴油的情况下,两头不见天,摸黑出工和摸黑收工是这里的常态。垦荒、耕耘、除草、下肥、收割、排渍、焚烧秸秆等,都靠肢体完成,都意味一个体力透支的过程。烈日当空之际,人们都是烧烤状态,半灼伤状态,汗流滚滚越过眉毛直刺眼球,很快就淹没黑溜溜的全身,在裤脚和衣角那些地方下泄如注,在风吹和日晒之下凝成一层层盐粉,给衣服绘出里三圈外三圈的各种白色图案。
驮一身沉甸甸的盐业收入回家,人们晃晃悠悠,找不到轻重,都像一管挤空了的牙膏皮,肚皮紧贴背脊,喉管里早已伸出手来。男人们吃饭简直不是吃,差不多是搬掉脑袋,把饭菜往里面哗啦一倒,再把脑袋装上,互相看一下,什么也没发生。没把瓦钵和筷子一并倒进肚子里去,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人们的鼻子比狗还灵,空中的任何一丝气味,哪怕是数里路以外顺风飘来的一点猪油花子香,也能嗖嗖嗖地被准确捕获,激发大家的震惊和嫉妒。
当时粮食平均亩产也就三四百斤左右,将其乘以全县或全省的耕地数就能知道,肯定不够吃,只能计划分配。男人每顿五两,女人每顿四两,如此定量显然只能填塞肚子的小小角落。如果没有家里的补贴,又找不到芋头、蚕豆一类杂粮,地木耳、马齿苋一类野食,就只能盼望红薯了。场部给每张饭票扣一两米,但红薯管饱。唯一的问题,是红薯生气,于是肠胃运动很多,红薯收获季节里总是屁声四起,类似偷偷摸摸的宣叙调或急急风,不时搅乱大家的表情。一场严肃的政治批判会上,应该如期出现的愤怒或深刻,常被一些弧线音或断续音瓦解成哄堂大笑。有经验的主持人从此明白,在红薯收获季节里不宜聚众(比如开会),不宜激动(比如喊口号),阶级斗争还是少搞点好。
这就不难理解,人们在工地上经常谈到吃。吃的对象、方法、场景、过程、体会一次次进入众人七嘴八舌的记忆总复习。不,应该说在刚吃过饭的一段,比如上午十点以前,肠胃还有所着落和依附,人们还是可以谈一些高雅话题,照顾一下上层建筑,比如知青们背记全世界的国名,背记圆周率或平方表,背记一些电影里的经典台词……来自《列宁在十月》《南征北战》《卖花姑娘》《广阔的地平线》什么的。但到了腹中渐空之时,“看在党国的分上”一类不好笑了,“让列宁同志先走”一类也不好玩了,肠胃开始主宰思维。从北京汤包到陕西泡馍,从广州河粉到南京烤鸭……知青们谈得最多的是以往的味觉经验,包括红卫兵大串联时见识过的各地美食。关于“什么时候最幸福”的心得共识,肯定不是什么大雪天躲在被窝里,不是什么内急时抢到了厕位,而是饿得眼珠子发绿时一口咬个猪肘子。
操!吃了那一口,挨枪毙也值呵。
这一天,我没留意时间已经越过危险的上午十点,仍在吹嘘自己的腹肌。但大甲把我的肚皮仔细审查,决不容许我用四个肉块冒充八个肉块,也不容许肥肉冒充肌肉。
“你也肯定没有110。”他说。
“怎么没有?我前几天还称过。”
“你称的时候,肯定喝足了水。”
“还憋了三天屎尿吧?”
旁人开始起哄。赌!赌!一定要赌!……这使我奇怪,体重这事有什么好争的?争赢了如何?没争赢又如何?直到大甲高高兴兴在地上拍出几张饭票,我才恍然大悟:阴谋原来在这里。
关于要不要刮去鞋底的泥块,关于要不要摘下帽子和脱下棉衣,关于要不要撒完尿再上秤……我们争议了好久。争到最无聊时,大甲居然说我头发太多,蓄意欺骗党和人民,因此必须减除毛重半斤。看看,半斤毛重,心思够狠毒吧?总之,在他们花样百出恶意昭昭的联手陷害下,我从秤钩上跳下来,听到他们一阵欢呼,眼睁睁地看着八张饭票被大甲夺走,然后给帮凶们一一分发。
这是不是下流无耻,我不想控诉。我只是第二天上工时再下战表:“公用鳖,我们比一比认繁体字。赌十张饭票,一张票三个字。”
“那不行。要比就比俯卧撑。”
“比投篮?标准距离,一人十个球。”
“你想反攻倒算?好,老子同情你,给你这个机会。这样吧,你当大家的面吃一块死人骨头。”他指了指身边一堆白花花的碎片,是大家开荒时刨出来的。
我掂了掂一片碎骨,觉得阴气袭人,污浊发霉,有一种咸鱼味,但我嘴上还得硬。“十张饭票太少了。”
“你不敢吃就是不敢吃。”
“我脑膜炎?你要我吃我就吃?”
“我赌二十张!”
“我今天没兴趣……”
“二十五!”
其他人觉得有戏可看了,围上前来,七嘴八舌,手舞足蹈,大加评点或挑唆,使大甲更为得意地把赌注一再加码。三十,三十五,四十,四十五,最后涨停在五十--如此惊心动魄的豪赌已让我呼吸粗重。
五十是什么意思?五十就是五十钵白花花米饭,意味着你狼吞虎咽时的晕眩,你大快朵颐时的陶醉,还有抚摸肚皮时的脑子一片空白。想一想吧,至少在很多日子里,你活得出人头地,光彩照人,活脱脱就是当今皇上,不必再对食堂里的曹麻子谄笑,让他的铁勺给你多抖落几颗黄豆;也不必捶打邻居的房门,对屋内的猪油味贼心不死抓肝挠肺;更不必为了争抢一个生萝卜,与这个或那个斗出一身汗。
生死抉择,成王败冠,翻身农奴得解放,不就在此一拼吗?我抹了一把脸,大声说:“有什么了不起?饭票拿来!”
他们被镇住了,好一阵沉默。
我清点饭票,确认赌资无误,然后旋旋腰,压压腿,捏一捏喉笼,咧一咧牙口,把自己当做出场前的运动员。我闭上眼,想一想舍身炸碉堡的英雄,想一想舍身堵枪眼的英雄,过一遍电影里诸多动人形象,在精神上也做好准备。最后,我用衣角细细拭去一块片骨上的霉污泥迹,两眼紧闭,大喊了一声:
“毛主席万岁--”
一次深呼吸之后,我咔哧咔哧地大嚼猛咬,没觉出就义是什么味,也不敢去想就义是什么味,直到胃里突然一阵恶涌,眼看就要涌上口腔,像高压水枪一样把嘴里的骨渣喷射出去,这才拔腿狂奔,蹿到附近的小溪旁一头扑下去,在那里拼命呕吐和洗漱--逃蹿前当然没忘记一把抓走地上所有的饭票。
从这一刻起,皇上的幸福令人陶醉,攥紧在手中的一沓饭票简直是镇国玉玺。晚上,队长买猪娃回来了。队长姓梁,绰号“秀佬”和“秀鸭婆”,不知有什么来历。他听说此事,觉得问题严重而且形势危急,立即把全队人召集在地坪,没顾得点上一盏油灯,就在黑糊糊的一圈人影里开骂:“连先人都不放过呵?什么人呢,就不怕遭雷打?也不怕吃得嘴巴里生疔?就不怕烂肠子烂肚?就不怕你婆娘以后生个娃仔没屁眼?”
黑暗中的责骂声在继续:“陶小布,你看你,长得十七八九二十一二三四岁了,还像只三脚猫,不上正版!”
这也太夸张了吧?一口气滑出七八个数,铆足了劲给我拔苗助长,怎么不一口气把我拔成一个老前辈?
“你锄死了花生苗,我还没说你。你一锄头下去,就少了半斤花生,明白不?你是个枯脔心,打牛--是你那样打的?你爹妈是那样打牛的?你爹妈是那样教你打牛的?你吃饭,它吃草。你睡床,它睡地。你跟它有仇呵?”
这话不但离题,还有点费解--他似乎不知道城里没有牛。
其他农民兴高采烈,会后一再点头哈腰笑脸逢迎,争相找我借饭票,又忍不住好奇地打听:那骨头到底是什么味?是不是有点酸?是不是有点咸或者涩?年纪稍长的几个,问过以后还心重,还嘟囔,看我的目光不无异样。我喝过水的杯子,他们决不再沾。我用过的脸盆,他们决不再碰。到了深夜,同房的一个老头从噩梦中惊醒,大喊大叫,满头大汗,找到梁队长强烈要求换房,说他情愿睡牛栏,也不同啃尸鬼同住一窝。只有食堂里的曹麻子好像很欣赏我:“小子,你胆大。以后吃烂肉算你的。”
他没解释“烂肉”是什么。
作为一种惩罚,我和大甲都被梁队长勒令去山里买竹。这是一种重活,得挑担子行走七十多里山路,不死也要脱层皮的。由于没拿到竹木砍伐指标,虽是给集体办事,但也算违规违法,只能贼一样昼伏夜行以求躲过沿途检查站那些关卡。我们这次去又遇上大雨,还没赶到产竹地,便在路边一位木匠家避雨,吃光了随身所带的几斤米,不知道接下来两顿饭的着落在哪里。
木匠是做棺材的。工房里摆了几口刚上过漆的胖大家伙,有木料味和油漆味,黑幽幽的阴气袭人。有时棺材板会无端发出炸裂之声,大概是板材干燥后变形所致,足令我们心惊肉跳。大甲喜欢这种阴森的布景和声效,一定要在这里睡觉,一定要在这里掌灯打牌,而且老是眉飞色舞。“喂,你后面的棺材里怎么伸出了一只手?”
一个绰号“光洋”的说:“大甲,你自己后面有一张女人的脸!”
“哈,是你的相好吧?来偷看我的牌?”
“真的,你回头看看,看看么。真的有一张大白脸,抹了口红,眼角流血,舌头尺把长,牙齿绿幽幽,哎呀呀我怕……”
我用一根食指封嘴,“别闹。好像有动静。”
我们屏住呼吸,确实听到了什么。但竖起耳朵再往深里听,能听到窗外下雨,树梢在摇摆,溪流轰鸣声膨胀,主人在隔壁的咳嗽有一下没一下……但这些都不关棺材什么事。直到一张木门突然咣当震响,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才吓出一片齐声惊叫。
原来是一阵风吹开了门。
灯火飘忽更加微弱,我们虚虚的不再敢回看身后,更不敢探身门外,出门撒尿也相约一起行动,你盯上我,我看住你,撒尿时不再有比谁射得更远或更高。突然,我们都感觉到赤裸的脚心一阵发麻,两腿不由自主地弹向空中--事后才明白电光与雷鸣同时抵达的恐怖意义:我们被击中了?
重新点亮油灯后,更多的震怒雷击接踵而至,一次次把窗外的夜晚照亮如昼。大水狂泼,地动山摇,整个世界黑白相续暴放暴收忽有忽无,似乎正万劫不复地向某个方向倾斜和滑落。又一道响亮的钢鞭抽下。一个火球滋滋滋地从大门外跳入,吓得我们叫的叫,倒的倒,蹿的蹿,无不灵魂出窍。待回过神来,发现火球没有了,但门边一堆碎瓦散泥,是从屋顶垮落下来的。空气中有刺鼻的焦糊气味。室内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大概是火球经过之处,有些地块久久地发烫。一个扫帚变成了灰烬,只剩下秃秃的一根棍。一个空油漆桶竟成了废铁皮,收缩成瘪瘪的一个铁瓢。
我们刚才若不是蹿得快,躲过了雷公爷这一“火轮车”(木匠的说法),眼下也会成为几团黑糊糊的烤肉吧?
我们整顿表情,心有余悸,陷入了激烈的互相指责。我一口咬定是他们刚才胡言乱语,对棺材不敬,触怒了阎王爷,才遭受如此严厉的警告。大甲当然更愿意相信是我吃了死人骨头,发了死人财,几十张不仁不义的饭票被雷公爷紧紧盯上了,害得大家差一点受连累,一把扑克也玩不好……最后,他们一齐起哄,把我当成扫帚星,祸根子,危险万分的轰炸目标,决不容许我同他们挤睡在一起。我只好夹了一捆稻草,在愤怒的指责声中去厨房那边另打地铺。
六年后的一天,我总算得到一个招工的机会,如愿以偿返回城市,结束了自己的知青身份。当时秀鸭婆早已离开茶场,回到他的村子去了。听说我要走,他一大早还是赶来送行,往我衣袋里塞了两个硕大惊人的鹅蛋,还有一堆板栗,又挑上我的被包和木箱,一直送到公路口。“你们这些城里仔,不是这个八字,其实本不该来的。” 他叹了口气,“看看这一坡坡茶树,这些年苦了你们,也苦了你们父母。”
“没什么。”
“男子汉嘴大吃四方,但吃死人骨头那事,以后不能再搞了。听见没有?”
“你还记得这事?”
“不管什么时候,都要靠自己一双手,靠自己做。”
“当然。”
“你们有文化,是干大事的人。不过,万一哪天你们在外面不好混,就回来吧。这里没什么好东西,但有我们的一口干,就不会让你喝稀。”
“我知道。”
“你晓得的,我们眼下也有水泵了,有碳铵了,有薄膜了,有喷雾器了,还杂交了……”他是指正在推广的杂交水稻种。
“梁队长,你的意思是,可以多打些谷子了吧?”
“就是,就是,肯定不会再饿你们了。你往后就是拖家带口的来,锅里也不会空着,桶里也会有的。”
我眼眶有点发热,去溪边洗了一把脸。早春的溪水还是透骨凉,一沾就好像手指头都被铰掉。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书在角色塑造上的突破性值得大书特书。它摒弃了传统文学中常见的“好人”与“坏人”的二元对立,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灰色地带。书中每一个重要人物,无论其行为多么令人不齿,作者都赋予了其极其合理、甚至可以说是动人的内在逻辑。你会在痛恨某个角色的决定的同时,又无法自拔地理解他为何会走到那一步。这种对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和软弱性的全然接纳,使得作品充满了道德上的灰色张力。我记得其中一段关于“责任”的探讨,没有长篇大论的说教,而是通过几个关键人物在绝境中的选择来呈现,那种选择背后的沉重、妥协与挣扎,远比任何哲学论述都来得更具说服力。这本书成功地将我们带离了道德的制高点,迫使我们直面自身也可能拥有的阴暗面。它探讨的不是“应该怎样”,而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人会变成什么样”,这种对现实的赤裸裸的揭示,使得整部作品具有了强大的现实批判力量,也让它在众多文学作品中显得如此与众不同,深刻而难以磨灭。
评分读完这本书,我有一种被一股强大的情感洪流席卷过的感觉。它不像那些流水账式的叙事,而是充满了强烈的象征意义和寓言色彩。作者的语言风格是那种带着泥土芬芳和陈年老酒味道的,朴实却极具穿透力。我尤其欣赏他对“孤独”这一主题的探讨,不是那种矫揉造作的、刻意渲染的悲伤,而是那种根植于生命本质的、带着宿命感的疏离。书中的人物命运,常常是在看似寻常的生活细节中悄然走向不可逆转的岔路口,而这些细节的处理,没有丝毫刻意煽情,却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例如,某次宴会上的一个不经意的转身,或是对一件旧物反复摩挲的描写,都像是埋下的微型炸弹,在后续的情节中静静引爆,带来阵阵回响。这种叙事策略,考验着读者的耐心,也奖励着那些愿意细细品味的读者。每一次情绪的起伏,都像是被作者精心安排好的音符,在恰到好处的时机触动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它不是读完就丢弃的快餐文学,而是会沉淀下来,在你独处之时,反复浮现、值得反复咀嚼的“精神食粮”,那份厚重感,非同一般。
评分这本书的视角转换简直是神来之笔,它打破了传统叙事的线性思维,让整个故事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近乎立体投影的形态。你永远无法确定下一个章节会从哪个时间点、哪个角色的意识深处切入,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张力。作者似乎对“记忆”的不可靠性有着深刻的理解,不同角色的回忆常常是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否定的,这迫使读者必须自己扮演侦探和裁判的角色,去拼凑出一个尽可能接近真相的画面。这种互动的阅读方式,极大地提升了代入感。我感觉自己不是在旁观故事,而是在和人物一同经历着认知的重构。特别是那些环境描写,并非简单的背景交代,而是成为了人物心理状态的外化,一座腐朽的钟楼,一片永恒静止的湖面,都仿佛拥有了自己的呼吸和秘密。这种“万物有灵”的哲学观,在不着痕迹间渗透出来,使得整个文本的密度极高,每一句话都承载着双重甚至多重的意义。读完之后,我得花很长时间去整理思绪,因为这部作品需要你用整个心智去消化,而非仅仅用眼睛扫过。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极佳,仿佛作者是一位技艺精湛的指挥家,将情节的起伏、人物的情感波动以及环境的渲染,编织成一曲跌宕起伏的交响乐。开篇的几章,笔触细腻而克制,像是在薄雾中缓缓揭开一幅古老画卷,初时只觉朦胧,待到关键信息点如晨曦般刺破云霭时,那种豁然开朗的震撼感令人难以言喻。作者在构建世界观方面展现了非凡的功力,每一个设定、每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都深深植根于故事的肌理之中,而非生硬的背景板介绍。特别是对时间流逝感的处理,不同角色的经历被巧妙地交错剪辑,有时让人感到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有时又陷入漫长而痛苦的煎熬,这种对“度日如年”的精准捕捉,体现了作者对人类心理的深刻洞察。最让我称道的是那些无声的对话,人物无需多言,一个眼神、一个细微的动作,便能传达出千言万语的复杂情绪。这种留白的处理,极大地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每一次重读,似乎都能挖掘出新的层次和含义。整体而言,这是一次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结构之精密,仿佛一座由文字搭建而成的完美迷宫,引人入胜,让人沉醉其中,不愿离去。
评分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本书的氛围,那一定是“幽邃”。它不是那种热烈奔放的激情叙事,而是更接近于深海中的潜行,四周被巨大的压力和无尽的黑暗包围,偶尔有一束微弱的光芒穿透进来,带来的震撼比直射的日光更令人心悸。作者对于“悬念”的设置,达到了近乎残酷的境界。他不是通过情节的突变来制造紧张,而是通过对某一核心秘密的缓慢、极其审慎的揭示过程来折磨读者。每一次以为要触及真相时,作者总能巧妙地设置一个障碍,或者引入一个新的谜团,让你不得不跟随他深入更深的迷宫。这种对节奏的掌控,展现了作者强大的控制欲和叙事自信。他深知读者渴望什么,却又拒绝轻易满足你,这种“吊着胃口”的手法,反而建立了一种奇特的信任感——你知道作者最终会给你一个交代,但这个交代绝不会是廉价的廉价的甜腻结局。这种对叙事过程本身的尊重和挑战,让阅读成为一种探索仪式,而非被动接受信息。
评分活动价很便宜值得购买啊
评分我认为韩少功是一位有思想的作者,去年读过他的长篇随笔《革命后记》,很有思辨能力。
评分头哦谈论蘑菇街墨脱嘛?
评分为搞活动买的,书比较划算,买了好多
评分包装不错,质量也挺好的
评分到货很快,东西不错。。。。
评分塑封全新正品,好书推荐
评分老爸喜欢看,很好的一套书
评分感谢配送师傅服务态度好,感谢京东。赞!赞!!!!!!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eaonline.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大百科 版权所有

![名著名译丛书:绿山墙的安妮 [Anne of Green Gabl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627582/5524b3f5Nb6277ab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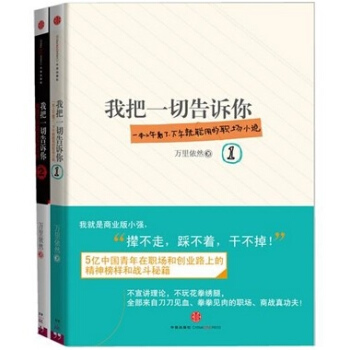



![从此以后 [Afterward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2173826/58eee49bNb5ed72ca.jpg)


![基本无害 [Mostly Harmles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356050/rBEhWlKhPxgIAAAAAAkaO5cPTgsAAGaQgInhYAACRpT007.jpg)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世界の終りと ハードボイルド?ワンダーランド]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443610/53a97e5fN170eccbc.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