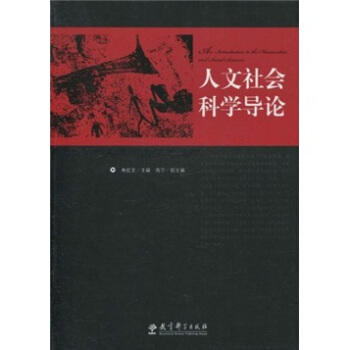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 西方中国科技史深入解析中国古代科学。
☆ 从中国古代科学看东西文化间的差异性。
☆ 凝练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之精华。
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科学》根据李约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举办的“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上的演讲集结而成。全书共五章。作者首先简要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概况及特点,接下来分别阐释火药和火炮的发明、炼丹术和医学发展的关系、针灸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史,最后就古代中国、欧洲时间观念的异同作了精彩论述。李约瑟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入手,充分挖掘古代文献,展现了古代东方技术和思想与西方的差异,及其如何通过阿拉伯世界对西方产生了影响。相较于学术性强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而言,这本小册子更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同时可激发对于东西方文化差异性的思索。
作者简介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年),英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他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李约瑟难题引起各界关注和讨论。
目录
序 言
前 言
第一章 导 论
第二章 火药与火器的壮丽史诗由炼丹开始
第三章 长寿之道的对比研究
第四章 针灸理论及其发展史
第五章 与欧洲对比看时间和变化概念的异同
附 录 中国历朝历代一览表
精彩书摘
中国与欧洲的思想差异
现在我将深入讨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天渊之别,我很想强调说明:中国哲学本源属于有机唯物主义哲学。从每个时代的哲学家和科学思想家发表的声明中都可以找到例证。中国哲学思想从不以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为主,至于机械主义世界观则甚至从未存在。中国的思想家普遍赞同有机论观点,即每一现象都遵循其等级次序与其他现象相互关联。可能正是这种自然哲学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例如,如果你早已坚信宇宙自身也是一个有机整体,那么就不会诧异磁石指北、指向北极星(或曰北辰星)、指向北极的现象了。换言之,中国人是一群喜好把理论投入实践的先行军,这或许可以解释何以中国人早早就了解到海洋潮汐的真正起因。早在三国时期(220—265年),就可以找到有关超距作用的惊人记载:不经任何物理接触,就可以跨越远距离空间完成某种动作。【此处似指左慈在许昌为曹操取到松江鲈鱼和四川生姜的故事,见《后汉书·方术列传》。】
前文中我们曾提到,中国人的数学思维与实际应用以代数为主,而非几何。中国文化中没有自发产生欧式几何,无可置疑,这一缺憾稍许阻碍了中国光学研究的前进步伐——反过来说,中国人也没有受到希腊观点的干扰,他们荒谬地认为光线是从眼睛里发射出来的。大约在元朝,欧式几何已传入中国,但直至耶稣会士入华之后才落地生根。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没有欧式几何的指导,许多重大的工程发明并未因此大受影响,它们依然取得成功,其中就包括利用精巧的齿轮制造的以水为动力的极为复杂的天文演示与观测仪器。其中还涉及我们先前探讨过的旋转运动与纵向运动相互转换的问题。
钟表内部构造的发展就要涉及擒纵装置的发明,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机械装置,其作用在于减缓一组齿轮的运转,以便与人类最原始的钟表,即天空的每日时间变化统一。有趣的是,中国的技术初看似乎纯粹是从经验中得来,其实不然。1088年,苏颂在开封成功地建造了水运仪象台,而此前他的助手韩公廉专门著述了一部理论方面的专著,书中详尽介绍了齿轮组与整座机械结构是如何从基本原理出发得到的。没有欧式几何,他仍然做到了。无独有偶,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密宗僧人一行59和梁令瓒在8世纪初制造的那一台水力机械钟身上,它比欧洲最早出现的机械钟及其摆杆机轴擒纵装置(verge-and-foliot escapement)早了六个世纪。此外,虽然中国没有培养出自己的欧几里得,中国人却依旧能够发展出这些在天文学上具有同等重要价值的发明创造,并坚定不移地付诸实用;这些古代发明甚至胜过了近代天文学,直至今天仍在全世界广为应用。同样,中国的赤道仪也并未因此停滞不前,最终一台精致的观测仪器问世了,虽然仪器内部只不过安装了一根观测筒,还谈不上望远镜呢。
前文中已经提到过波粒二向性问题。秦汉以来,中国人始终关注的原始波动理论,和自然界两大本原“阴”与“阳”永恒的跌宕起伏关系密切。2世纪开始,原子理论一次次地传入中国,然而这些理论始终未能在中国科学文化的沃土上落地生根。虽然缺乏这一特定理论的指导,中国人依旧取得了许多奇妙的成就,例如中国早在西方人之前几百年就认识到雪花的晶体结构为六方晶系。【《太平御览》卷十二《韩诗外传》:“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独六出。”】同样,在建立有关化学亲合性问题的基本知识上,中国人也并未受到阻碍,这些知识出现在唐、宋、元时期一些关于炼丹术的论述中。某些概念的缺失反倒是减少了阻碍,毕竟直到欧洲文艺复兴之后这些理论才真正对近代化学的兴起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兼重实践与理论
有人认为,从根本上说,中国人注重实践,不太相信理论。我并不想同这一观点进行辩论。但我们必须当心,不能无限制滥用这一论点。11—13世纪期间,宋明理学(Neo-Confucian school)取得了空前成就,他们成功地实现了哲学上的集大成,与此同时,欧洲经院主义哲学也熔于一炉,这难道不是很奇妙吗?甚至可以说,不愿埋首理论研究、尤其是几何学理论的做法给中国人带来诸多裨益。例如,中国天文学家从不像欧多克索斯(Eudoxus)和托勒密那样推导天体,但却避免了宇宙由同心水晶球构成的假定,而这种假定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始终占有统治地位。16世纪末,耶稣会的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到中国,在寄回国内的一封信中他声称中国人怀有大量愚蠢的念头,其中特别提到中国人不相信水晶天球的存在;然而,不久之后欧洲人自己也摒弃了这一观点。
从根本上追求实际,并不意味着精神上就可以轻易满足,因为中国古代文化中进行过大量细致入微的实验。若非风水师极为认真地观察磁针指示的位置,人们永远不会发现磁偏角现象;如果不是温度的测量与控制上的一丝不苟,以及对窑内氧化还原环境的任意调控,制陶工业就永远无法取得成功。人们对这些技术细节所知较少主要出于社会因素,致使能工巧匠们掌握的秘诀不能公之于世。不过我们还是能不时找到某些文字记载,例如1102年问世的《木经》(一部木工手册),就是一本建筑学方面的经典,后来的《营造法式》就是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木经》的作者是著名宝塔匠人喻皓;此书一定是他口述而成。他虽然不识字,却仍然能把自己所知所学传给后人。另有一例就是广为人知的《闽省水师各标镇协营战哨船只图说》(Fukien Shipbuilders’Manual),这部举世稀有的珍贵手稿表明,造船匠人有一些识文断字的朋友,他们熟知工程术语,可以将工匠们所能告诉他们的内容全部付诸笔端。
科学发展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
至此,我们面临的是有关社会与经济的问题,我将乐于利用本次讲座的最后几分钟探讨这些问题,因为在中西方科学、技术与医学的比较研究中,这些悬而未决的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如果事先没有意识到东西方的传统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的显著差异,就绝不可能理解两者在科学、技术与医学的不同。我深感欣慰的是,尽管不同学者对中国的封建社会解释大有分歧,但学者们总体上认为在过去两千年里,中国并不具备像西方那样军事贵族制的封建体制。无论中国的政治制度究竟是不是有如马克思主义奠基者们所知那样应当称作“亚细亚生产方式”,或是(像其他人的说法那样)称作“亚洲式官僚主义”,或是“封建官僚主义”,还是称作“官僚主义封建制度”(“二战”期间我在中国时,中国朋友们常常喜欢用的说法),抑或无论哪种你自己更乐于接受的名目,中国的制度势必与欧洲人心中所知有所差异。
我曾一度认为,这是由于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天下初定时中小城邦封建领主全部消失了。天下,一人之天下,国家由唯一的封建君主统治,也就是皇帝本人,他手中握有相对膨胀的权力工具,利用职位不能世袭的官员和士族文人中选拔出来的官僚或称官吏操纵天下,搜刮民财。这些官员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称作一个“阶级”实在令人难下定论,因为显然在不同朝代、不同程度上可变性极强。如果愿意的话,许多家族可以全族升入士族“阶层”,再从中脱离出去,尤其是当科举考试在选拔官员问题上举足轻重的时代。科举考试与行政管理需要特定的天赋与技巧,家族中若不能培育出这类人才,在上层社会就难保一两代昌盛。因此,士,即文人官僚,两千年来一直作为国家的文化与管理精英。我们一定不会忘记“唯才是举”的理念,许多人认为这句话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然而这一思想并非法国人所开创,甚至并非诞生于欧洲,实际上这一观念在中国已历千年。18世纪时欧洲盛行摹仿中国大潮,亲华之风正盛。尽管19世纪时这种风尚已渐渐失势,人们也不再把天朝大国及其官场视作培育圣贤的殿堂,我们还是可以在某些篇章文字中找到这样的介绍:19世纪时,西方诸国正是在深刻了解中国的科举考试先例之后,才将这种选官竞争理论引入欧洲的。当然官僚也并非如我们有时理解的那样完全不分阶级,因为即使在最为开放的极盛时期,也是家学渊博、私人藏书丰富的公子们占有优势;然而无论如何,博学多才的行政官员的价值标准也必然与利欲熏心的商贾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是亘古不变的事实。
而这又是如何影响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复杂的问题,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就不作深入探讨了。然而毋庸置疑,以士族学者看来,中国的某些科学才是正统科学,其余则不算。由于需要勘定历法,天文学一直是正统科学之一,这是因为中国根本上属于农业国,历法的制定格外重要。此外人们崇信占星术,只是这一点没有农业需求那样重要罢了。人们认为只有在博学大家的工作中数学才有用武之地,某种程度上也会用到物理学,尤其在官僚核心人物才特有的工程建设项目中,数学和物理学将大有帮助。中国官僚社会需要建设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与水土保持工程,这不仅意味着古代学者普遍认为水利工程建设确实利国利民,而且表明它有助于稳固现有社会形态,而学者们自身就是这种社会形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远古时代起,兴修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往往会打破封建地主领地的疆界,其结果就是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以皇帝为首的官僚中央政府。许多人都坚信中国的封建官僚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这一事实。实际上,某些文本中确实可以找到类似的阐述,例如公元前81年的《盐铁论》。书中有一页提到:天子必须考虑广阔疆土上的水利工程需求,与别的封建地主相比,天子要耗费更多心力。【《盐铁论 园池第十三》:“大夫曰:诸侯以国为家,其忧在内。天子以八极为境,其虑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县官开园池,总山海,致利以助贡赋,修沟渠,立诸农,广田牧,盛苑囿。”】
炼丹术则有别于这些应用科学,它显然属于非正统的科学,是与世无争的道家术士和隐士们特有的工作。这一领域中丹药本身并不引人注目。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孝道,于是炼丹成为文人墨客心目中的高尚研究,事实上儒医们确实愈发投入这项研究;另一方面,炼丹与药学的必然联系又将它与道士、炼丹术士以及药剂师联系到一起。
最后,我相信大家已经发现,早期中央集权的封建官僚社会体系有利于应用科学的发展。比如地震仪就是其中一例,前文中我已不止一次提到过。在那极为久远的年代里,地震仪可以与雨量计和雪量计相媲美。而且极有可能是因为中央统治机构期望能够预见未来现象,这种合乎情理的要求促进了上述这些发明创造的问世。例如某一地区发生了严重地震灾害,就应当尽早得知这一消息,以便派人救援,并且给当地政府派遣增援部队以防骚乱。同样,设置在西藏山岳边缘的雨量计也能发挥很大作用,人们据此确定应当对山体下方的水利工程采取怎样的保护措施。中古时期,中国社会完成了同时代社会中最伟大的远征探险,其有组织的科学野外作业也是为数最多。佳证之一就是8世纪早期由一行(前面曾提及此人)和南宫说主持的子午线测量。这次地理测量跨度不少于两千五百公里,跨越了自印度支那至蒙古的广阔疆土。几乎与此同时,一支远征队受命开赴东印度群岛,以便观测南天极20°以内的南部星空。我怀疑同一时代的其他国家政府是否有力量投入如此辽远的长途勘测活动。
从早期开始,中国的天文学就受益于政府的支持,然而天文学研究只具半公开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利的。有时中国史学家也认识到这一点,如晋朝断代史《晋书》中就有一篇有趣的文字写道:“天文仪器自古代已经付诸使用了,由钦天监官员密切监控,代代相传。因此其他学者无缘研究这些仪器,从而导致非正统的宇宙论得以流传四方,格外兴盛。”【《晋书 天文志》:“此则仪象之设,其来远矣。绵代相传,史官禁密,学者不睹,故宣、盖沸腾。”】然而,这一论题不能言之过甚。无论如何,我们清楚地知道宋朝时与官僚统治息息相关的文士家庭中已然可以进行天文学研究了,甚至相当普遍。例如,我们知道苏颂少年时,家藏小型浑天仪模型,于是他逐渐理解了天文学原理。【朱弁《曲洧旧闻》卷八:“独子容(苏颂字子容)因其家所藏小样而悟于心。”】时隔一百年,哲学大家朱熹也家藏一具浑天仪,并且尝试重新构造苏颂的水力转仪钟,只是没有成功。【《宋史 天文一》:“朱熹家有浑仪,颇考水运制度,卒不可得。”】除此之外,还有某些时期,例如11世纪,文官科举考试中数学与天文学知识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前言/序言
本书中各篇文章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举办的第二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讲演的原稿。对那次访问中的点点滴滴,我依然记忆犹新:诸如学术同仁的盛情款待,学生们的聪慧与求知热情,沙田校园内外与众不同的美景,以及如此切实地体会一座不凡的中国城市给我带来无时不在的震撼,都让我难以忘怀。我期待这些讲稿中揭示的史实能够帮助东西方读者更公允地评价中国文化领域中科学、技术与医学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
四十三年前,我开始致力于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当时我并不了解自己的研究是否有用。如今《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的许多卷册已经出版,但仍有更多作品尚未完稿,有待出版。我们把这些稿件分为“天上”与“地上”两部分。前者即原创方案,是我们认真而愉快地漫步于科学领域时制定的整体性方案。当时无法判定的是,针对不同科学形式,即纯科学与应用科学,应当分别投入多大力量;正因如此,某些“天上”的书籍才有必要分成几大类出版。它们实际上都是“地上”的有形书籍。如今已有十一册作品或已付梓,或行将出版,余下还有八九册尚未完工(编者按:迄今该丛书已出版了七大卷共二十五册)。我已是八十一岁的人了,如果可以干到九十岁,我将至少有半数机会亲眼目睹这条巨轮驶入终点港湾。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今后即将出版的许多卷册现已草成,只是仍有许多地方需要编辑、润色。除此以外,我们在世界各地拥有二十多位合作者,他们共同努力取得的成就远非一两个人可以媲美。
在此我必须说明,没有中国朋友们的鼎力合作,我们将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在我看来,无论中国人或是西方人,都无法单独完成这项事业——其专业知识与技能要求实在过于巨大。因此我要纪念以下这些人士:头一位是我的中国老朋友鲁桂珍(按:1992年辞世),她在剑桥大学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任副馆长;第二位是我的第一位合作者王静宁先生(按:1994年辞世),在冈维尔凯斯学院 (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那间狭小的工作室里,他与我共同工作了九个春秋。此外还有许多人的名字应当提及,如先后在新加坡、吉隆坡、布里斯班和香港工作过的何丙郁先生,加利福尼亚的罗荣邦先生,纽约的黄仁宇先生,芝加哥的钱存训先生,以及最近加入的屈志仁先生,他主要研究陶瓷工艺部分。我无法一一列举每个人的名字,其中也并非全是中国人。欧洲合作者中我想提一下曾在牛津和砂拉越(Sarawak)待过的乐品淳(Kenneth Robinson)先生,波兰的雅努什 赫米耶莱夫斯基(Janusz Chmielewski)先生,以及法国的梅泰理(Georges Metailie)先生。此外大西洋彼岸还有在费城工作的席文(Nathan Sivin)先生,哈佛的叶山(Robin Yates)先生,以及多伦多的厄休拉 富兰克林(Ursula Franklin)女士。就如实际情况所示,我们构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跨国群体,事实本身已然预示着我们将拥有美好的前景。因为无论还有其他什么工作要做,这项事业都应当无可置疑地视作增进各民族相互了解的尝试,因而也成为通向世界和平友好之途的重要阶梯。
回首四十年前,那时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习惯晚上沐浴时阅读《左传》。当时只有古典作品可供研究,这一情景让我铭记至今。通过这种阅读,我牢牢记住了上一个世纪和本世纪上半叶那些伟大的汉学家们的著作,诸如沙畹(edouard emmannuel Chavannes)、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伯希和(Paul Pelliot)、夏德(Friedrich Hirth)、福兰阁(Otto Franke)、翟理斯(H. A. Giles)等人。与今天相比,那时学者所著的译本为数太少了。那时我们把所有这类书籍都搜集起来,汇入图书馆。可是看看今天,差别何其巨大啊!我们的新书架在各种各样的论文与专著的重负下呻吟不绝,如宋代水利工程研究、从汉朝到明朝的造船技术研究、古代中国的医学伦理等等,不一而足。我认为除非我们的确只是推动西方人更全面研究中国文化的历史运动中的一部分,否则就以促进了有价值的作品得以流通而言,我们自己也称得上有功之臣。然而中国在革命之后,国内研究也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西方考古学家们抱怨说,中国的考古学报告雪片般纷至沓来,把他们都埋在报告堆里了。有关科学史、技术史和医学史等各方面的书籍纷纷出版,书中确有种种重大发现。回首往昔,我们曾是这一伟大潮流中的一部分,或许还是先锋力量,为此我非常快乐。
最近,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刊物《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的编辑们为我们的作品组织了一期专刊。他们言道,为寻找投稿人而大费周章,因为西方世界里在中文和科学史两方面都有造诣的专家几乎无不参加了我们这个群体;事实上他们的确从中发掘出笔力不凡的写作人,如伊懋可(Mark Elvin)、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李倍始(Ulrich Libbrecht),以及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就如学刊主席所说,人们对这期专刊的评价褒贬不一。不过,我还是对某些半苦半甜的评论兴致极高。例如,有人把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和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做了一番比较,暗示有迹象表明我们的陈述中已经悄无声息地潜入了某种主观意识成分。无论如何,我乐于接受这一评价,因为我认为无论谁在进行如此浩繁的跨文化研究工作时,都会自然地将自己的信仰体系投射于其中,这是他向同代人和后人布道的机会(我有意选用“布道”这个说法)。假若何时我们像律师辩护一样有倾向性地写作,或者何时过于强调中国文化贡献,那就是在刻意找回平衡,以弥补以往极端否定它的这种过失。我们力图挽回长期以来的不公与误解。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全书某一册的前言里,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句子,如今读来仍然觉得有趣。“实质上,一段时间以前”,我们谈道,“一位并非全然敌视这套珍贵书籍的评论家这样写道:该书根本上依据不足,原因如下。该书作者坚信(1)人类社会的进步令人类对自然界逐渐增进了解,并渐渐提高了对外部世界的控制能力;(2)这一科学具有终极价值,随着将它付诸实际应用,构成了各民族文明的统一体,不同文明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是相当的……在这个统一体中有如江河之水源源不绝、奔流入海;(3)伴随这一前进历程,人类社会正逐渐演变成更为宏大的统一体、更为复杂的事物、更为不凡的组织。”所有这些反面评价的根据,我们都视作自家论点,如果我们也有一扇过去的维登堡那样的大门的话,我们一定会毫不迟疑地把这些话钉在门上。如今我可以坦言,这位评论家就是已故的芮沃寿(Arthur Wright)先生。他确实堪称诤友,只是他崇信佛教的超脱凡尘,对政治态度悲观,这使得他在世界观方面与我们大相径庭。
总而言之,这套丛书本质上是一次次最为激动人心的探索。我们从未奢求使它成为任何学科的“盖棺定论”,因为在工艺领域,这种断语绝无可能,即使今天依然如此。然而搜寻工作依旧时时动人心弦——认可某些思想意识;在陌生的术语下发现始料未及、本应预先考虑的事物;迎来意想不到的先驱,并对他们的作品大感钦佩;以及理解以往从未揭示的发明和技艺。这一切都那么令人激动。人们会借用《道德经》上的话说,“大道废”时,对“能”与“不能”的评价便会无处不在。那时“声”与“希声”的差别也就显而易见了。让我们在下几个世纪到来之前完成这一终极的平衡吧。我们所知的是,我们已然在科学、技术和医学领域幸会中国过去二十五个世纪以来的兄弟姐妹,尽管永远无法与他们交谈,我们还是可以时常读到他们的文字,并寻求契机回馈应予的荣誉。
李约瑟
1981年1月21日
用户评价
这是一部需要反复研读的典籍。我最欣赏它处理细节的严谨性,以及作者在面对历史空白和争议时所持有的审慎态度。他从不武断地下结论,而是倾向于展示所有可能的解释路径和支持的证据链条,将最终的判断权交还给有思考能力的读者。书中对古代历法体系复杂性的描述,简直是一门艺术,将天体运行的精确计算与哲学上对“天人合一”的理解完美地焊接在一起。对于那些希望真正了解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如何观察世界、如何建立其认知体系的人来说,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最扎实、最全面、也最富有人文关怀的入口。它不是简单的知识罗列,而是一场关于人类理性如何在中国特定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深刻对话。
评分我不得不承认,最初翻开这本厚重的著作时,心里是有些忐忑的,毕竟“学术讲座”这四个字往往意味着枯燥的理论堆砌和佶屈聱牙的术语。然而,实际的阅读体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本书的行文风格极其灵动,仿佛一位经验丰富的大家,在你面前缓缓展开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每一个转折和细节都处理得恰到好处。它不像是一本教科书,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文化之旅。作者在引经据典的同时,又非常注重历史叙事的节奏感,高潮迭起,引人入胜。我特别留意了其中关于古代天文学观察记录的部分,作者通过对不同朝代观测数据的比对分析,揭示了古代观测者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不断精进的技艺,这种基于实证的论证方式,让人无法辩驳,只能由衷赞叹。这本书真正做到了将深奥的学术内容,转化为了引人入胜的知识普及,实属难得。
评分说实话,这本书给我最大的震撼,是它打破了我长期以来对“古代科技”的刻板印象。过去总觉得,古代的成就多集中在文学、艺术或哲学领域,而科学技术方面似乎总带着某种“粗糙感”或“神秘色彩”。但这本书用详实的数据和无可辩驳的考古发现,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认知框架。作者对古代冶金术和水利工程的分析尤其精彩,他没有停留在描述“建造了什么”,而是深入探讨了背后的力学原理和材料科学认知,这完全是站在现代视角对古人智慧的深度致敬。文字的密度非常高,信息量极大,我不得不经常停下来,反复咀嚼那些关键的论断和引用的史料,生怕遗漏了任何一个精妙的论证环节。这绝对不是那种可以轻松“扫过”的书籍,它要求读者带着敬畏和专注去对待每一页纸上的文字。
评分这本书真是令人大开眼界,我原本以为自己对中国古代的某些技术和思想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但读完之后才发现自己过去的认识是多么的肤浅和片面。书中对一些经典文献的解读,比如那些晦涩难懂的古籍,作者竟然能用如此清晰、生动的语言将其阐释出来,让我这个非专业人士也能轻松领会其精髓。尤其是关于早期数学思想的探讨,作者不仅梳理了从萌芽到成熟的脉络,还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哲学思潮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那种将技术、文化和历史紧密结合的叙事方式,极大地增强了阅读的代入感。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那些跨学科议题时所展现出的深厚学养,他总能敏锐地捕捉到不同领域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出一个宏大而又严谨的知识体系。读完后,我仿佛重新站在了历史的某个关键节点上,去审视那些奠定了后世文明基石的智慧光芒。
评分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其深厚的跨文化视野。它不仅仅是在梳理中国古代的科学进展,更重要的是,它巧妙地将这些进展置于世界文明的大背景下去审视。我注意到作者在讨论到某些技术传播或思想交流的节点时,会非常自然地引入同期其他文明的成就作为参照,这种对比分析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理解维度。它让我们明白,人类文明的进步并非孤立的,而是相互启发、相互竞争的复杂过程。尤其是关于古代医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部分,那种对生命现象的观察和归纳能力,放在任何时代都是顶尖的智慧。这本书的结构设计也十分巧妙,逻辑层次分明,每完成一个章节,都会有一种对前文知识点融会贯通的豁然开朗之感,让人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下一部分将揭示怎样的奥秘。
评分古代科学,这套书很不错,值得收藏
评分…………………………
评分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中国古代科学
评分购物首选京东,宅男不用出户
评分很好看
评分很好看
评分¥29.30
评分还奥还奥还奥还奥还奥还奥还奥还奥还奥还奥还奥
评分购物首选京东,宅男不用出户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eaonline.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大百科 版权所有












![书面语篇的世界:体裁研究 [WORLDS OF WRITTEN DISCOURSE A GENRE-BASED VIEW]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0030043/a6e24753-9cc0-4982-a779-18dc9d68f96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