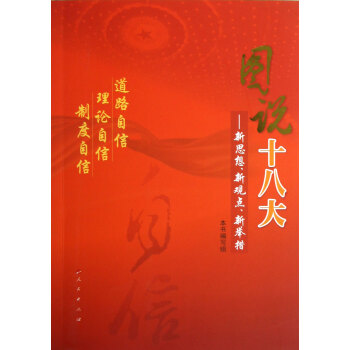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塔列朗自述》不仅是一部模拟的自传,而且是一部鲜活动人的小说,讲述了塔列朗生活过的18世纪和19世纪的人和事,从1754年到1838年,从路易十五到路易—菲利普。这也是共和制法兰西在欧洲棋盘上为对抗各国王朝联盟而进行博弈的棋局的注释,这一系列的联合,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目的明确,分合迅速,总体上反映了现代史的各个阶段,也是塔列朗政治生涯中波澜壮阔和起伏不定的各个阶段的体现。内容简介
《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塔列朗自述》系塔列朗回忆录的简洁版。塔列朗在十九世纪初期是法国绝对的风云人物,法国政权的一次次更迭中他始终屹立不倒,甚至几乎每次政权更迭背后都能隐隐看到他的手腕。他总能在时势变动之际看到大势之所趋,然后在背后推动此大势,从而在新局面下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其经略手腕绝对一流。塔列朗在维也纳和会上凭一己之力,将众矢之的的战败国法国重新带入强国的行列,堪称奇迹。作者简介
塔列朗(1754~1838),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出身贵族家庭,当过主教。1789年大革命时期,为三级会议和制宪会议代表。1792年奉命出使英国。英法开战后逃往美国。1796年返回法国。1797~1807年历任督政府、执政府、第一帝国和复辟王朝初期的外交大臣(部长)。1814年4月任临时政府首脑兼任外交部长,1814~1815年出席维也纳会议时,竭力利用同盟国间的矛盾,改善法国的地位,曾提出“正统主义”原则。1815年7至9月再次任临时政府首脑。1830~1835年在驻英国大使任内,竭力促进英法接近,并参与决定许多国际问题。他以野心勃勃、权变多诈著称,为19世纪初资产阶级外交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法国外交之父。王新连退休外交官,1964年毕业于外交学院,在外交部和我驻外使馆从事外交工作38年,同时进行写作和翻译,退休后仍笔耕不辍。现为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会员,外交部老干部笔会(外交笔会)理事,参与外交笔会几本文集的撰稿。出版翻译作品:《乌弗埃一博瓦尼的政治生涯》(合译)、《政治厩房——法国社会丑闻》(合译)、《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主译)、《非洲民主化浪潮中的华裔外交部长》、《永恒的玩具》(合译)、《美国制造》等。目录
“观恒丛书”总序“经略译丛”序言
敬告读者(代序言)
一、我的自述
我为什么要写回忆录
二、我的枕边书
原则与信条
外交官的学校
三、青年时代
我的出生
我的童年
四、伏尔泰
五、德·巴里夫人的圈子
孔蒂王子
路易十六的加冕礼
显贵会议
六、法兰西大革命
三级会议
联邦的弥撒
米拉博
七、英格兰
八、美利坚
九、督政府
德·斯塔埃尔夫人
十、格朗夫人
十一、波拿巴
埃及战役
我的财富
雾月十八日
蒙特隆
执政府
马尔迈松
我之罪
十二、拿破仑
皇帝的婚礼
剑与笔
分道扬镳
喜剧
悲剧
入侵
十三、复辟
莫布勒伊
十四、维也纳会议
十五、百日政变
尼撒王
塔列朗府邸
大布尔乔亚
十六、查理十世
十七、七月王朝
伦敦会议
十八、退休生活
雷纳尔的赞歌
最后一幕
译名对照表
精彩书摘
九、督政府德·斯塔埃尔夫人1795年6月。长达两年中,没有任何行动,令人厌倦的流亡生活就要结束了的时候,在我即将动身去东印度的前夜,热月出现了,就像天空中的一片彩虹,说它像一束北极光,更加确切。最后的一次动荡将罗伯斯庇尔斩首示众。革命的火山不再喷发,但是,一缕青烟表明它尚未熄灭。我向国民公会写了一封请愿书,要求回到法兰西,我也向德·斯塔埃尔夫人写了信,对督政府表示了好感:“假如我在这里待上一年,我就会死去。”她受到了感动,设法让玛丽—约瑟夫·谢尼埃支持我的要求。革命悲剧中两个敌对的兄弟之一的这个人的赞歌,并没有完全抹杀安德烈的讽刺诗。约·谢尼埃先生作了一个报告,提醒人们我对祖国的服务,这与其说是为了我的事业,不如说是为了他的兄弟的事业,由此,我得到了一份回国的法令,从而结柬了我的流亡生活;为此,我也打心眼里原谅了他对我的讽刺挖苦:心灵手巧的莫里斯,一瘸一拐地走路也那么雅致,对精神饱满之人,他予以教训;对冷酷无情之人,他则诚心诚意地为伍;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他行事方式绝然不同。
武断专制的执政党内,他插上了可耻的一脚,另一只脚,却一直在反对党内,而这只脚,却是一只跛足。
内克尔小姐(即德·斯塔埃尔夫人)的童年与青少年是幸福的,受到了良好的道德教育,她甚至不愿在她母亲的公狗面前梳妆打扮,而宁在她父亲的母狗面前更衣;因为她们都是雌性的,她可以无所顾忌地脱光衣服。
德·斯塔埃尔夫人对她父亲的崇拜是真诚的;但是,她将这种崇拜推至极致,颇具有戏剧性,看起来是极其夸张的,因为,在他的面前,她的地位就是安慰他退休后的衰老,而不是寻求她沙龙的成功。真的,“孤独令20岁的灵魂感到恐惧。”但是,她两者兼而有之,而且倍感欣慰。
作为一个书信体作家,日内瓦的德·塞维涅夫人,并没有被天空耀眼的不同的阳光弄得盲目。她的风格,就是男人,她同他们进行交谈。在她的沙龙里,与尽量让她的忠实拥戴者辉煌的莱斯皮纳斯小姐相反的是,她让她的爱戴者暗淡无光,自己处在谈话的中心。她对每次谈话都进行精心的谁备,以便让谈话产生演讲的效果,这样一种工作让她心力交瘁,加快了她的死亡。
1796年。真正的流亡,并不是远离祖国,而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活,却在国内找不到任何值得爱的东西。一只羊,被拴起来,就只有以拴它的绳子为半径来吃草,我没有什么值得过分抱怨的。在什么山,唱什么歌,因势利导而已。
“不幸随地随时存在,但幸福也是如此。”自从我回到国内,我就没有了影响,也没有金钱,这对于我来说,是双重的灾难。人们常在街上遇见我,见我瘸着一只脚,彳亍而行;可是,每天早晨在客厅里等待见我的,仍然不下40余人,我的起居仍然像王子一样。
我的弓上只有一根弦,这就是德·斯塔埃尔夫人,我向她敞开心扉,开诚布公。
“我亲爱的孩子,我只有25路易了;这不够一个月的开销;你知道,我又走不了路,至少我该有一辆车。假如你没有办法让我体面地过生活,我宁可去自杀。安排一下吧;如果你还爱我,你就该这样做。”在与戈贝尔相处的过程中,“助理主教的格言与莫里修道士的圣油壶”,屡试不爽,让我获得成功,在与德·斯塔埃尔夫人相处中,它们更是让我获益匪浅,你瞧,她开始运作了。
“再见到我之前不要作出任何决定;我要将天地翻过来,作为开始,我先去找找巴拉斯。我向他提点什么要求呢?”“一个对外关系部的名额;一旦置身于该部,我有办法谋得一个位子。
”她马上展开了战斗。
向他的同事们谈这件事之前,巴拉斯需要见见我,我就动身到苏莱斯纳去,他在那里有一栋休闲小屋。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在晚饭前,我们进行了交谈。他告诉我让督政府接受一位贵族、王子、主教是多么多么困难。在我们谈话过程中,有人急忙来告诉他,他的爱子在河里洗澡时淹死了,他当着我的面号啕大哭,丝毫不掩饰他极度的失望。
那时,我默不作声,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说;但是,从我克制的态度和我的目光中,他明白了我尊重他的痛苦。他最终慢慢安静下来,重新面对我,一上了饭桌,政治话题开始了,我们海阔天空地谈了一会儿,他就决定支持我。
从1792年到1795年,可以说没有什么外交;那时,外交的机制与语言是毫无用处的,就像一只被暴风雨击毁的轮船,罗盘已毫无用处一样。代表法兰西讲话的人是夏尔·德拉克鲁阿、比绍、德福尔格、勒布伦一通迪之流,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就像对旧衣服一样。
比绍是一位小学教师,是作为临时雇员被招到图尔耐勒码头的。1808年,他向我写信,说他病了,住在收容所中,没有经济来源,我让人给了他6000法郎的补贴。我得到了补偿,这个职业是不应该被毁坏的,没有人能够预见到未来的某一天财富的车轮不会将他辗得粉身碎骨。
夏尔·德拉克鲁阿部长也没有取得成功;外国的大使与外交官们对大革命时的处事方式与习惯感到不那么舒服。法兰西拥有一些成为征服者的将军,她也应该拥有一些这样的外交家。剑与笔,二者缺一不可,查理大帝就是用他的剑柄作为私章来给他的敕令加封的。
巴拉斯说服了大家,强调说我的能力是公认的,我被任命为对外关系部的部长。
1797年。我重新在巴黎安了家,住在了巴克路的加里菲公馆,那里十分宽畅,装修得相当华丽。
与此同时,法兰西研究院也向我敞开了大门,想起来我原来是该院的创始人,并曾经选举我为道德政治学科成员,还是那里的理事长。作为见面礼,我宣读了两份回忆录:《美国与英国的贸易关系》和《北美图表——革命后赎回新殖民地的利益所在》。下面就是我的论据:“代替旧殖民地,向那么多心有不甘的人们开辟道路与出路,他们需要一些项目与活动,也向那么多不幸的人们提供希望。”这让我想起困在纽约的无聊的时光,那是我与立法委员会成员布拉古侯爵共同度过的岁月。为了消遣,我们一起走遍了美国所有的城市。当了部长之后,我就建议我的流亡伙伴和难友回到法国来。布拉古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也是一个发了疯的赌徒;作为权宜之计,他要求我给他一个年薪600镑的职位,我不屑于接见他和答复他,并获悉,在生活所迫及债主催逼之下,他选择了自杀。我们两人共同的一个朋友对我进行了强烈的指责:“无论如何,你是布拉古死亡的起因。”我背对壁炉,打着哈欠回答他:“可怜的布拉古!”在督政府中,我与巴拉斯相处得很好;但是,勒贝尔却与我颇多龃龉,常常坏我的好事。他知道,坐在这样一架到处都是假砝码的天平的称盘上,一指之力就足以让欧洲的平衡倾斜。
在督政府的一次讨论中,他将文具盒甩向我,并大声叫喊:“丑恶的流亡分子,你的意识同你的脚一样,没有丝毫的正直感。”事后不久,斜眼的勒贝尔问我,事情怎么样了,我就回答:“倾斜着呢,就像你看到的一样。”拉雷维埃一雷波堤另一类型的闹剧。1794年,他在法兰西研究院宣读了一份关于有神博爱教和进行拜祭的新形式的回忆录。对于这样的癖好,我只有一种看法:为了创建他的宗教,耶酥基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并获得了复活;拉雷维埃也应该尽力去这样做。
巴拉斯同他们一起谋划了果月十八日的政变,牺牲了巴泰勒米和卡诺,前者主张迂回而行,而后者干脆反对这一图谋。
德·斯塔埃尔夫人被排除在外。她有一种共和党人的思想,有一批贵族出身的朋友,她处事谨小慎微也使她远离了这一图谋。如果说她果月十八日曾经工作,那么十九日就停止了。她在两个阵营之间妥协,她的行为与其说是巧妙的,不如说是勇敢的,她将朋友扔到水中,又将他们捞了上来。
我给予波拿巴的第一个节日,曾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曾引起人颇许多评论。
德·斯塔埃尔夫人处在这个圈子的中心,让这位年轻的恺撒中止了他的进攻:“将军,你认为谁是世界上的第一女人,包括死去的和活着的?”而他,以其战士的气概,回复一个赞赏:“是生孩子最多的那个。”上面就是互射的两枚火箭,都跌落在地上。应该将它们捡起来。
又有一次,是在一个晚宴上,我坐在德·斯塔埃尔夫人与雷卡米耶夫人中间,前者像赫耳弥俄涅一样阴沉着脸,后者像圣洁的阿莉茜一样面带微笑,她只让她的500个朋友爱她的上半身,而却让热拉尔画了她的全身像。
“……在一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机器中,“显现了人们从睡梦中获得的美丽。”在这幅肖像上,她显露出了一副天真无邪的神态,她自己很清楚需要坚持些什么。而在大卫为她画的肖像中,她面容严肃,有点怒不可遏的样子,好像她已经在思索丰特内勒的那句名言:“漂亮女人能死两次。”当邦雅曼·贡斯当跪在她的脚下,威胁要去死的时候,我也这样看她的。
“先去死吧,然后我们再看。”在思想与美貌的天平上,我失去了外交的手腕;它可能倾向于美貌一边多一点。
“最后,你看,”德·斯塔埃尔夫人说,一脸的不屑,“假如我们两个都掉到河里,你先救哪一个?”我没有正面接招:“噢,男爵夫人,我肯定您的游泳技术同天使一样好。”当她完成她了的小说《德尔菲娜》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她就是小说的主人公,而我,化身成了德·韦尔农夫人,一个贪婪、爱美、轻浮的女人。她问我对她的小说如何看,我就说:“大家都对我说,在小说中,你与我,都变装成了女人呢。”几年之后,乔治·桑夫人给自己起了一个男人的名字,她在她的《一个旅行者的通信》中,也粗暴地对待我,在那里面,她将我写成一个丑陋不堪的家伙。
人们画了一张漫画,我被画成跛足的爱神丘比特,看着被画成美丽之神维纳斯的德·斯塔埃尔夫人梳妆打扮,瞪着一双漂亮的眼睛,目光在优雅的天使身上巡睃。
她向我宣布离婚那天,我叹了一口气:“唉!”后来,她又私下告诉我,她又要结婚了,我就大叫:“太棒了!”她希望这次的结合是秘而不宣的;但是,她是那么的有名,好像她嫁给了波利什内勒老爷。
我对德·斯塔埃尔夫人一点也不忘恩负义;但是,正是为了品味爱一个愚蠢女人的幸福,才要去爱一个天才的女人。
……
前言/序言
“经略”一词,最早出于《左传·昭公七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西晋杜预注之曰:“经营天下,略有四海,故日经略。”由此可知,在古代,经略者必定是以天下为一彀,以四海为一家的。对于古代中华帝国是如此,对于古代西方帝国也没有差别——古代罗马帝国一统天下自不必说,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从理念上来说也是一个旨向全世界的普遍帝国。之所以如此,概因帝国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它是一种文明的道德理念的承载者,不拘限于特定领土,亦不拘限于特定人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进入中世纪晚期,西方开始经历一种深刻的历史变化。名义上大一统、至此已延续数百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系由种种复杂的封建契约关系捏合在一起,其各个封邦彼此之间有着激烈的竞争,在封邦夹缝中还有着各种各样的自治城市。这些因素缓慢但坚定地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现代法权治理的初萌。百衲布般的帝国无法整合这些新事物,一些强大的封建王公便在与市民阶层结盟的基础上,开始了现代领土国家的建立。这些新的政治体在理念上来说仍然是帝国的附庸,亦要受到夭主教会的挟制,其作为绝对自立的事物无法获得一般认可。于是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对这种独立于帝国与宗教之外的,对应于特定的领土以及特定的人民,高度世俗化的全新政治组织形式进行正当性论证。该种组织形式就是现代国家。他们的论证与强大王公的需求一拍即合,现代国家的质料与形式便全面地出现了,政界与学界的沟通与联动,是一种区别于帝国的、目标有限的“经略”。所以,“国家”(N撕on—state)是一种西方特殊性的产物,相当程度上也是人为的产物,而并非出于自然的人类一般组织形式——反倒部落和帝国才是出于自然的人类一般组织形式。西方建立了“国家”之后,开始对外扩张,并因此而将“国家”的理念传播到非西方地区,及至二战后的非殖民化进程在世界上普遍建立了“国家”,以致我们通常都以为“国家”才是人类政治组织的常态,这是一种深刻的误解。
该一误解对国人带来的一个负面后果就是,我们经常会以为“国家”无需维持而自然存在,以为天灾、人祸、战争、动乱,都不会取消“国家”作为一个自在主体的地位,所以,就政治问题而言我们只需关注政体。若持此种认识,实不足与论“经略”。须知,从普遍帝国当中脱颖而出的“国家”是近代政治当中最为基础的东西,其作为一个人造物恰是需要最高级的政治技巧来卫护的。政体的改革与变迁不过是二阶政治问题,若离开了“国家”这个一阶政治问题,则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国家”,这是最大的“政治”!对于“国家”的经略,方为现代世界最为根本的经略!对于何谓国家,国人尚多懵懂;对于国家该当如何经略,则更是需要深刻的反思。西方各国近代以来的大政治家,莫不是政治实践当中“国家学”的绝顶高手,看看他们是如何经略国家的,对于我们必会大有启发。非西方国家也有一些深谙现代经略之道的政治家,在他们的苦心经营下,自己的国家也在世界上获得了一席之地,这些人的作为,也必值得我们认真借鉴。西方的国家理论我国已多有译介,但是对于西方以及非西方的大政治家们的经略之道,则仍是关注有限。
虑及于此,我们选编了这套“经略译丛”,选辑的标准或是近代以来国外重要的政治家,其本人的著作,体裁不论;或者是对近代某些大国之总体战略筹谋的析解书籍。虽然所选书籍体裁不尽一致,但有一个旨向是一致的,那就是,选辑之书要能反映出作为个人之大政治家或作为整体之大国的政治思考与实践,从中能够读出其经略之苦心,以为我们的镜鉴。希望本套丛书的翻译出版能够在帮助国人理解现代国家经略这一问题上有所助益。
用户评价
《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塔列朗自述》这本书,给了我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它以一种极其个人化、甚至可以说是“自白”的口吻,将一位历史上极富争议的人物,呈现在我们面前。塔列朗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故作高深的理论,却充满了深刻的洞察和精准的判断。他坦然面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无论是担任神职人员的经历,还是在革命浪潮中的摇摆,亦或是辅佐拿破仑,最后又参与复辟,他都进行了真诚的剖析。我尤其欣赏他对“变色龙”这一比喻的深刻解读,他将其升华为一种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生存的智慧,一种懂得顺应时势,却又不失原则的生存之道。书中,他对于当时欧洲各国政治势力、外交策略的描绘,都显得极为生动和真实。读这本书,仿佛是在与一位睿智的长者对话,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揭示了政治的本质,以及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如何保持独立思考和清醒判断的重要性。
评分这本书,我愿意称之为“政治智慧的教科书”。《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塔列朗自述》不仅仅是关于历史事件的陈述,更是塔列朗本人对于政治艺术的深刻反思与总结。他以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性,剖析了权力运作的本质,以及在动荡时代,个人如何生存与发展的哲学。我被他描述的那种在复杂政治漩涡中,保持清醒头脑,并在不同阵营之间游刃有余的能力所深深吸引。他并非是那种一成不变的理想主义者,而是懂得审时度势,适时调整自己立场,以最大限度地保全自身和国家利益的实践者。书中的许多段落,都让我为他的远见卓识感到惊叹,例如他对于拿破仑帝国覆灭的预判,以及他在维也纳会议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都展现了他非凡的政治嗅觉和外交手腕。这本书让我明白,政治并非是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而是一门充满博弈、妥协与智慧的艺术,而塔列朗,无疑是这门艺术的集大成者。
评分不得不说,《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塔列朗自述》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对“政治家”这个词的刻板印象。过去,我总觉得政治家是严肃、刻板、甚至有些虚伪的代言人,但塔列朗的“自述”,却让我看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可能性——一种以极其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应变能力,在混乱中寻找平衡,在危机中创造机遇的艺术。书中,他对自己每一次身份的转变,每一次立场上的调整,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阐释。这种“变色龙”式的生存智慧,并非苟且偷生,而是一种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和对自身价值的精准定位。我特别欣赏他在描述与拿破仑、路易十八等风云人物交往时,那种不动声色的观察和评价,他似乎总能看穿对方的内心,然后以最恰当的方式与之周旋。这不仅仅是一本历史读物,更像是一本厚黑学的巅峰之作,然而,它又是如此的真诚,真诚得让人心惊。他坦然承认自己的野心,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妥协,这种真实感,反而让他的形象更加立体和可敬。读这本书,就像是在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深度对话,与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家进行思想的碰撞。
评分《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塔列朗自述》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冲击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以一种极其个人的叙述方式,打破了历史研究的冰冷感。塔列朗用他那富有洞察力的笔触,将自己置身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之中,他不再是教科书上那个遥远的名字,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考,有挣扎的鲜活个体。我特别喜欢他对于“忠诚”这个概念的理解,他并非盲目地效忠于某个王朝或领袖,而是将国家的利益、个人的声誉置于首位,并在此基础上,灵活地调整自己的策略。这种 pragmatism(实用主义)在当时的欧洲政治环境下,显得尤为珍贵。书中,他对于各种政治力量的分析,对于不同权力格局的解读,都显得鞭辟入里,极具前瞻性。他的文字中流露出一种洞悉世事的超然,仿佛能够预见历史的走向,并在这其中扮演关键的角色。这本书让我深刻体会到,真正的政治智慧,并非是强硬的对抗,而是巧妙的斡旋,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以最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达到最想要的结果。
评分读完《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塔列朗自述》后,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仿佛亲身经历了那波诡云谲的欧洲政治舞台。这本书以一种极其私人的视角,将塔列朗——这位在革命、帝国、复辟各时期都游刃有余的外交大师,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一直以为历史人物往往是冰冷而遥远的,但塔列朗的文字却充满了人性的温度和细腻的情感。他毫不避讳地剖析自己的动机,无论是对权力的渴望,对家族命运的考量,还是在关键时刻所做的艰难抉择,都展现得淋漓尽致。我尤其被他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那种在旧秩序崩溃、新力量崛起的巨大动荡中,如何保持冷静,伺机而动,展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和生存能力所折服。他对于不同阵营、不同人物的评价,既有深刻的洞察,又不失幽默,让人仿佛置身于他的沙龙,听他娓娓道来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政治博弈。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历史事件的复述,更是一堂关于人性和权力的生动课程,让我对“政治”二字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不再是简单的阴谋论,而是充满了对人性的洞察和对局势的把握。
评分为什么没有他在雅各宾党的时候的记述呢
评分直言不讳的变色龙.塔列朗一直是我感兴趣的人物
评分15岁时,夏尔中学毕业,父母没跟他商量一下,就把他送进了圣·秀尔比斯神学院。夏尔的哥哥童年就已夭折,所以夏尔已经成为长子,可是父母却剥夺了他承袭爵位和财产的长子继承权,硬要让他当神甫。在神学院的五年里,他仍然很少说话,不爱交友,既孤单又苦恼,把空余时间都消磨在图书馆里。当时能够找到的革命书籍,包括卢梭、伏尔泰的著作,他都读过。
评分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这时,塔列朗在其一生
评分好
评分直言不讳的变色龙.塔列朗一直是我感兴趣的人物
评分1754年2月2日,夏尔·莫里斯·塔列朗诞生在巴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里。他的祖先从10世纪卡佩王朝建立时起就已经是宫廷贵人了。按血统来说,他的父亲塔列朗伯爵查理-达尼埃尔同国王路易十六还是表兄弟!
评分今天刚刚拿到书,这本(法)塔列朗写的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塔列朗自述很不错,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塔列朗自述不仅是一部模拟的自传,而且是一部鲜活动人的小说,讲述了塔列朗生活过的18世纪和19世纪的人和事,从1754年到1838年,从路易十五到路易—菲利普。这也是共和制法兰西在欧洲棋盘上为对抗各国王朝联盟而进行博弈的棋局的注释,这一系列的联合,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目的明确,分合迅速,总体上反映了现代史的各个阶段,也是塔列朗政治生涯中波澜壮阔和起伏不定的各个阶段的体现。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塔列朗自述系塔列朗回忆录的简洁版。塔列朗在十九世纪初期是法国绝对的风云人物,法国政权的一次次更迭中他始终屹立不倒,甚至几乎每次政权更迭背后都能隐隐看到他的手腕。他总能在时势变动之际看到大势之所趋,然后在背后推动此大势,从而在新局面下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其经略手腕绝对一流。塔列朗在维也纳和会上凭一己之力,将众矢之的的战败国法国重新带入强国的行列,堪称奇迹。经略一词,最早出于左传·昭公七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西晋杜预注之曰经营天下,略有四海,故日经略。由此可知,在古代,经略者必定是以天下为一彀,以四海为一家的。对于古代中华帝国是如此,对于古代西方帝国也没有差别——古代罗马帝国一统天下自不必说,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从理念上来说也是一个旨向全世界的普遍帝国。之所以如此,概因帝国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它是一种文明的道德理念的承载者,不拘限于特定领土,亦不拘限于特定人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进入中世纪晚期,西方开始经历一种深刻的历史变化。名义上大一统、至此已延续数百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系由种种复杂的封建契约关系捏合在一起,其各个封邦彼此之间有着激烈的竞争,在封邦夹缝中还有着各种各样的自治城市。这些因素缓慢但坚定地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现代法权治理的初萌。百衲布般的帝国无法整合这些新事物,一些强大的封建王公便在与市民阶层结盟的基础上,开始了现代领土国家的建立。这些新的政治体在理念上来说仍然是帝国的附庸,亦要受到夭主教会的挟制,其作为绝对自立的事物无法获得一般认可。于是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对这种独立于帝国与宗教之外的,对应于特定的领土以及特定的人民,高度世俗化的全新政治组织形式进行正当性论证。该种组织形式就是现代国家。他们的论证与强大王公的需求一拍即合,现代国家的质料与形式便全面地出现了,政界与学界的沟通与联动,是一种区别于帝国的、目标有限的经略。所以,国家(撕—)是一种西方特殊性的产物,相当程度上也是人为的产物,而并非出于自然的人类一般组织
评分直言不讳的变色龙.塔列朗一直是我感兴趣的人物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eaonline.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大百科 版权所有











![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0876037/9a91f776-335a-477b-999e-1474cc35aee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