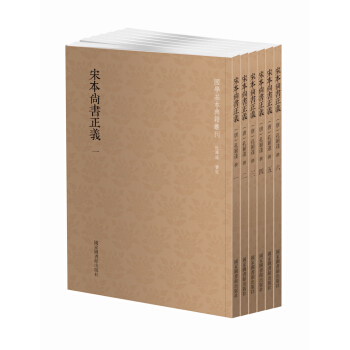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在复旦读书时,竺可桢与陈寅恪不仅是同班,尤为难得的竟是同桌。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与陈寅恪的首次晤面,由于竺是管理科学院研究所的领导,陈寅恪坦率地谈到他对华罗庚的不满。
1962年陈寅恪与竺可桢探讨天象“五星连珠”与时局女主崛起之关联,可以说是找到了华山论剑的真正高手。
1966年3月20日,这两位当年同桌共读的双子星座最后一次相晤,一位病卧在榻,一位行色匆匆,自此一别,“文革”如山洪暴发般汹涌逼来,此生再无相见聚首之日矣。
内容简介
竺可桢与陈寅恪是大学同班同桌?陈寅恪对华罗庚不满?陈寅恪与竺可桢都认为1962年的天象“五星连珠”与时局女主崛起有关联?著名文史学者张荣明教授,以竺可桢的日记为依据,从中钩沉出竺可桢与陈寅恪的种种交往,及双方对同时代人的评论、对时局的解析。期间的许多故事均为前人所未注意。全书图文并茂,观点故事甚为新奇但又查有实据。
作者简介
张荣明,1952年生,华东理工大学教授,著名文史学者,上海十大藏书家之一。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研究,近年尤注重晚清民国人物研究,已在海内外出版《中国古代气功与先秦哲学》、《方术与中国传统文化》、《从老庄哲学至晚清方术》、《庄子说道》等十多部学术著作。目录
引言一、1949年前的竺可桢与陈寅恪
二、1949年后的竺可桢与陈寅恪
附录:
陈克艰:陈寅恪不会这样建议
张荣明:究竟是谁向蒋介石提建议?
精彩书摘
竺可桢的回忆正确无误。三十多年后复旦大学校史组在旧档案中发现了相关记录资料:“本刊讯:最近,校史组在残存的我校一九。八年、一九。九年档案中,发现了已故著名学者陈寅恪和竺可桢当年在复旦的学习成绩记录。他们当时……都是十九岁,一同编在丁班。……陈寅恪是丁班第一名,考试成绩为94.2分,也是全校各班考试成绩的魁首;竺可桢是班上第四名,成绩为86.6分。”(1984年2月24日,《复旦校刊》第108期,转引自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第54页,中华书局,2010年)大师丰采果然不同凡响,青少年时代皆已头角崭露。值得一提的是:竺可桢与陈寅恪不仅是同班,尤为难得的竟是同桌(《竺可桢日记》第10卷,1958年4月21日;《竺可桢全集》第15卷79页)。由于天公不作美,历史老人没有把司马迁与张衡、司马光和沈括撮合在一起作幼时同窗伏案共读,没有提供史学大师与科学巨擘早年联桌共读的先例,因而令后人无法遐想竺、陈这两位双子星座当年同桌共读的奇妙景象。不过,这两位青少年大抵慧光毕露,彼此映照,故尔也惺惺相惜,意气相投。后来的事实表明:竺、陈青少年时代的同窗之谊被两人终身珍视和不懈呵护。
1936年4月,竺可桢在南京,曾赴中央研究院开评议会:“九点至总院开评议会,评议[员]缺席者周鲠生、陈寅恪、姜立夫及李仲揆四人。上午推定翁咏霓为秘书,叶左之为评议员,以代替在君。”(《竺可桢日记》第1卷,1936年4月16日;《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56页)这次评议会陈寅恪与数学家姜立夫、地质学家李四光(仲揆)皆未出席。此年4月,陈寅恪正在清华大学授课,故无暇南来赴会。会上增补叶左之为评议员,以代替不久前逝世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君)。
1936年8月,已经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致函陈寅恪、傅斯年,托觅俞大纲“至高工、高农为国文教员事”(《竺可桢日记》第1卷,1936年8月20日;《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132页)。俞大维、俞大纲兄弟两人皆是出身名门、富有才华的学者,陈寅恪的妹妹是俞大维的夫人,傅斯年的太太又是俞大维妹妹,彼此皆是姻亲,故竺可桢拟聘俞大纲至浙大教授国文,先要托陈、傅两人代为说项。8月25日,竺可桢收到“陈寅恪函”。8月26日,“下午接傅斯年函,知俞大纲可就高工、高农教员,即发聘书”(《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134页、135页)。
2.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因病于香港逝世。3月下旬,中央研究院在重庆开第五次评议会,商讨推选新院长,“五点至美专校一号晤陈布雷,遇晓峰,谈及蒋先生提出以顾孟余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事,余谓恐评议会中通不过。余表示决辞浙大。七点至外宾招待所Hostel,叔永与咏霓请客,到唐臣、竹铭、陈寅恪、姜立夫、郭任远等卅人。膳后作一Straw vote民意测验投票,[试]院长人选。咏霓得2l,适之20,骝先19,余仲揆6,稚晖先生、农山、孟真、君[员]武与余各得一二票”(《竺可桢日记》第2卷,1940年3月21日;《竺可桢全集》第7卷第321页)。
顾孟余(1888—1972)曾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铁道部长、交通部长,显然是一位国民党中枢要角。因此,蒋介石希望由顾孟余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顾孟余虽为高官,但在学术上并无重要创树,故竺可桢认为“恐评议会中通不过”。陈寅恪对于院长人选亦持独到见解,“三月廿一日,(陈寅恪)先生出席评议会秘书翁文灏、研究院总干事任鸿隽晚宴。先生即席申述院长人选必为国际学术界知名学者,选举院长必须尊重各人自由意志”(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第199页,中华书局,2010年)。临大事而不苟,充分显示了陈寅恪一贯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念。
中央研究院评议员皆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学识与风骨俱佳,并不唯国民党最高首领蒋介石马首是瞻——既然意见有分歧,餐后就试作一个“民意测验投票”,结果是翁文灏得21票,胡适之20票,朱家骅19票,顾孟余连一票都未得。
次日,评议会正式召开:“八点,评议员陆续来,计到立夫、企孙、左之、晓峰、郭任远、焕镛、农山、步曾、淬廉、寅恪、咏霓、雪艇、骝先、唐臣、润章、子春等。院中各所长均到,惟巽甫未来。林可胜于下午始到。推雪艇为主席。行礼如仪,为蔡先生致哀。次叔永报告蔡先生逝世前得病情形。八点五十分休息。九点十分又召集会议。来宾到居觉生、陈立夫及中央党部代表杨公达。读林主席及蒋委员长训辞后,居院长及陈部长各有演说。次评议会秘书咏霓及总干事叔永均有报告。”“晚七点半至中四路103号官邸,应蒋介石先生之邀晚膳。出席评议员除仲揆、缉斋、雪艇及林可胜四人以外余均到。蒋对于未见过诸人一一问询。询余以浙大搬何处,学生全到否。”(《竺可桢日记》第2卷,1940年3月22日;《竺可桢全集》第7卷第321—322页)蒋介石在官邸设宴招待此次赴重庆开会的评议员,并特别与初次见面的评议员一一交谈,以示礼贤下士。值得关注的是,陈寅恪与从未谋面的蒋介石近距离相晤之际,为国家大局发展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建议内容在本书后半部分将会拈出讨论。
……
前言/序言
1.神童的出现,自古以来总会引起世人一阵惊愕、歆羡、嗟叹以及随之而来众星捧月似的赞赏及传颂。北宋大儒程颐曾遇见一个卓荦不凡的十龄之童,不禁赞叹:此儿“日后必成大器”。五年后(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这位少年一鸣惊人,考中进士,参加廷试并荣获第三(俗称探花)——在孔子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年龄却已早早取得如此骄人的态势,这样的履历在一部廿四史中亦属罕见,可谓天上麒麟儿,人间俏神童。十多年后,这位青年才俊出使辽国,因功而晋爵为“淮宁伯”。将近半个世纪后,南宋大儒朱熹为这位当年的英俊少年写下了一篇《宋淮宁伯竺简行状》。
孟子曾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此言系针对一个民族而言。对于一个家族来说,或许九百年方能再降生一位享誉中外的人杰。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上虞人,中国气象学界和地理学界一代宗师。早年系哈佛博士,中年为浙大校长,晚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浏览过竺可桢的4卷文集及通读完他的16卷日记之后,笔者深感这是一位西方自然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罕见博雅人物,也是一位在传统“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中皆有建树的卓越人物。
综观其一生,竺可桢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几乎可说是绝无仅有之异数,得到国共两党领袖在不同时代的器重。他早年出洋镀金,留学哈佛,具有知识学问上的强大优势,归国后又具有深厚的政治资源,国民党高官邵元冲、蒋作宾是他的姻亲,国民党大佬吴稚晖是他的远亲(《竺可桢日记》第5卷,1946年9月11日;《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204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因此盛年能够大有作为,在科研与教育领域创造辉煌业绩,一展平生抱负。否则即如才华卓绝的钱锺书,由于时运不济,中青年只能坐困“孤岛”上海,赋闲在家,纵然写出瑰奇的《围城》和精湛的《谈艺录》,当时也得不到相应的评价。此即诚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1949年之前,由于竺可桢的学术威望及卓越成就,加上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猖獗横行一时(傅斯年对此曾痛加贬斥及辛辣嘲笑),身为大学校长的竺可桢身不由己被入国民党(《竺可桢日记》第4卷,1944年8月24日;《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171页),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竺可桢日记》第14卷,1968年7月8日;《竺可桢全集》第19卷第161页)。笔者认为:当年国民党党部对于大学校长的强行“党化”——这种违背个人意愿的挟持“入党”,无疑可以视作是一种政治上的绑票。但在20世纪50年代几乎是“汉曹不两立”的国共尖锐对峙期,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沉重的政治包袱。身负如此沉重累赘历史包袱的竺可桢,1949年之后仍奇迹般地被器重,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多次接见及宴请交谈,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19个显赫职务(《竺可桢日记》第9卷,1957年《杂记》;《竺可桢全集》第14卷第736页)
2.
七百多年前,元世祖忽必烈两次派遣大军发动声势浩大的海上远征,如果具备一定的气象学知识,则后来屡屡侵华肆暴的化外蛮横之徒日本岛国或许早已成为中华帝国的一个“海北岛”,从而与海南岛遥相呼应,打造成一根包括台湾岛在内的环太平洋珍珠项链,以拱卫我五千年传承的熠熠煌煌华夏文明,亦不致明代以降屡遭倭寇小毛贼频频骚扰。
历史不是童话,时光亦无法倒流,否则的话,忽必烈的大元王朝只要有幸敦聘一位竺可桢式的气象学专家——试看天下谁能敌,曾经横扫欧洲的蒙元大军,挥戈东征,那支成吉思汗当年弯弓射大雕遗留下来的倚天长柄青铜镝,必将像烤羊肉串或冰糖葫芦串似地洞穿日本列岛,东亚的版图及疆域区划亦将随之焕然一新,何劳前几年日本某位有点见识的政治家苦心孤诣地提倡“脱欧归亚”,以致引起大洋彼岸自由女神裙下的山姆大叔一阵惊慌,深恐卵翼之下降伏多年的东详小武士脑生反骨挣脱羁绊要重争自由与独立呢?
时至20世纪,气象学对于国防建设及军事战争仍然具有举足轻重、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1932年,竺可桢撰有《天时对于战争之影响》一文,详述天气变化对历史上东西方几次著名战争成败之影响,指出:“十九世纪德国名将穆尔克(Von Moltke)每临战阵,必亲测气压之高下、风云之方向,日以为常。”至近世第一次世界大战,飞机轰炸、大炮射击,毒气施放以及舰队海战之成败亦与能否精确预测气象变化有莫大关系(《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112—116页)。1943年,竺可桢阅读到一批海外军事情报资料,这些资料再次证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气象预报对于英国飞机轰炸德国柏林发挥了难以想像的重要作用:“阅《英大使馆情报》十二月一日,British EmbassyBulletin December 1,1943。p.5有关于英机炸柏林之气象情报。谓精密之天气预报,对晚间大规模之轰炸,如上周英机之轰炸柏林,实为必要。Manchester Guardian《曼彻斯特卫报》谓,民卅至卅一年,英轰炸机常在途中遇到不测风云,其危险不亚于德国之防空。嗣后天气预报进步,上周之柏林轰炸,若非有高度技术之天气预告,决不能得如许之成功。凡每次长距离轰[炸],必须有来回途中及目的地之天气预告,并须有高空飞行层之风速、温度、达冰点之高度以及云层之有无及高下。轰炸之成功,赖有此耳。”(《竺可桢日记》第3卷,1943年12月7日;《竺可桢全集》第8卷第684页)
因此,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原应归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气象局将由军方接管(《竺可桢日记》第6卷,1949年11月22日;《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573页),也就顺理成章了。
作为中国现代气象学的奠基人和领导者,竺可桢的满腹经纶及专业知识,对于国家民族的发展不可或缺,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政府同样重要——两种不同类型的政府皆需倚重于他,这是一种历史必然,他的学问具有超越不同意识形态的宝贵价值。其次,自1918年至1949年,竺可桢在中国教育领域与科研领域呕心沥血,取得了卓越成就,形成了巨大的学界声望。1949年是新旧社会嬗变交替的一年,一切皆在方死方生之间,呱呱坠地的新生共和国的科学建设及种种草创,尤为需要一位像竺可桢这样能够承先启后、凝聚各方俊杰的领导人物。前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指出:“他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分管生物和地学领域,在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原有基础上,领导重新组建了一批新的研究机构,以其在科学界和教育界的声望,在实现平稳过渡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秦大河主编:《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120周年文集》第4页,气象出版社,2010年)这段话字斟句酌,是极为周详、妥贴、客观的评述,完全吻合历史的真相。
如果允许在此讲得稍稍夸张或活泼一点的话,就是:当1949年共产党军队“百万雄师过长江”之后,一位身背“国民党中央委员”历史包袱的知识分子要想从旧的社会进入新的社会中安营扎寨、贡献才华、受到器重——平稳穿越20世纪冰火两重天,他必须要具有超越常人犹如达摩“一苇渡江”的真本领。
竺可桢对于气象学、地理学及科学史夙有精深的研究,对于物候学、气候变迁以及自然资源考察等领域皆有筚路蓝缕的开创性贡献。作为自然科学家,他的文史修养,他对经史子集的娴熟及造诣在同行中可说是首屈一指。竺可桢在教育思想与办学理念方面所具有的深邃眼光及宏大气魄,较之近代杰出教育家蔡元培(笔者拟作“竺可桢与蔡元培”一文阐发之)绝不逊色。尤其是早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他统领浙大师生进行教育史上罕见的四次大转移,“在敌机的轰炸下,在敌寇的炮声中,坚持教书育人,锐意科研创新,体现了一种危难之际弦歌不辍勇猛精进的民族坚毅精神,终于把浙大办成腾誉国际的‘东方剑桥”’(拙文《抗战前的预测与抗战中的预言(一)》,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156期,2011年9月18日)。令人不由想到这是一位恰如西哲所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的人物。
3.
可笑的是胡适怀抱皮相之见,目睹青年时代的竺可桢清癯瘦弱的身形,竟然断言他活不到20岁(《竺可桢日记》第11卷,1962年2月28日;《竺可桢全集》第16卷第21l页)。出口伤人之际的胡适虽属年青稚嫩,但出身于徽州诗书礼仪之家的胡公子莫非就忘记了文学大家苏东坡对于汉初张良的那段精悍的评论:“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留侯论》)张良是为数百年汉王朝开国奠基的首位关键战略家,曾受到汉高祖刘邦的高度赞赏而被封为“万户侯”。以世俗之见想来,此类豪杰必然是位魁梧的伟丈夫,或至少是像卧龙诸葛先生那样气宇轩昂的人物,但司马迁当年“至见其图,状貌乃如妇人好女”(《史记·留侯世家》),似乎身形柔弱如妙龄女子的张良的气概与其盖世勋业不相匹配,然而恰恰正是这种看似弱不禁风却神志清明洞察天地风云的身躯及大脑中方能进发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惊人智慧,故苏东坡一锤定音加以强调:“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20世纪,陈寅恪与钱锺书是两座风景迥异的学术高峰,两人的学术成就及影响已为学界所公认,但以笔者一家私见来看,在人文艺术领域(这里暂且把弈技按照传统观点归入“琴棋书画”一类的艺术范畴),这个世纪还出现了两位以一敌万的顶尖天才人物:一位无疑是鲁迅,另一位则是吴清源(关于吴,笔者根据掌握的一些新资料将写一篇专文)——然而这两位旷代天才皆是弱不胜衣、体重不满百磅的清癯人物。
严守古典传统惯于讥嘲胡适的国学大师黄侃(1886—1935)却别具眼光,他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室楼梯之间偶尔邂逅青年竺可桢时,竟然青眼相加,说一声:“这小子倒还不错!”(刘季友:《黄季刚先生对革命的贡献》,载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第103页,三联书店,2006年)此话口吻语气固然不雅,但恰如鲁迅所喜欢的那副郑板桥对联所言:“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黄侃的国学素养深厚精湛,连风鉴之术也怀抱独家之秘,他仅惊鸿一瞥,便能断定眼前这个竺姓小伙子将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较之胡适的皮相之见,委实高明不可以道里计。
这或许还是一个道统对政统可以分庭抗礼乃至不屑一顾的年代。才大如海的黄侃面对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张继,因一言不合当即翻脸痛斥,张乃仓皇逃去(《黄侃日记》1933年10月24日,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笔者按:黄侃《日记》每日同时标出阴、阳历,本文所引仅出示阳历),过后还来陪酒重修旧好。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党部秘书长丁惟汾,或许他自觉才疏学浅却又要附庸风雅,于是常常向黄侃这位学界尊神送款送礼,屡邀饭局,不惜仰其鼻息殷勤示好(《黄侃日记》1934年2月15日、7月4日)。原来山东军阀韩复榘拉拢山东籍大佬丁惟汾主编《山东通志》一书,丁氏盛邀黄侃大驾光临青岛一次,以便为编写此书发凡起例。孰料黄侃回信说“患痱且须理书”,并“辞不赴青岛”(《黄侃日记》1934年7月9日、10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理由竟然是“患痱且须理书”,令人不禁莞尔,这大概也只有在《世说新语》中才能看到的魏晋风度了。
国学大师黄侃面对国民党权贵彰显如此矫矫不群之丰采,以三家村内冬烘先生目光观之这似乎有点欠敦厚,但或许在孔子看来,这是尚未彻底礼崩乐坏而犹存一丝古风余馨的年代中权势向学问谦卑鞠躬致敬的最后一个范例。
学术慧命之所在,即为道统尊严之所在;文化学术慧命乃一国国脉之所系,托命之人岂可妄自菲薄哉!德国大文豪托马斯‘曼曾经声称:“我之所在,即为德国。”黄侃胸中嵌崎磊落之气喷薄而出,仰天长吁化为虹,诚可与日尔曼民族这位四海云游的大文豪的精神气度遥相辉映。
援此而论,平生睥睨天下的黄侃对于猝然相觏的青年竺可桢独施青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殊遇。
大抵是感于国学大师的某种善意罢,青年科学家竺可桢与黄侃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由相识而结下了不同寻常的友谊。这一年是1919年,竺、黄两位皆在该校任教(《竺可桢传》编辑组著:《竺可桢传》第333页,科学出版社,1990年;司马朝军、王文晖合撰:《黄侃年谱》第14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927年,竺可桢来到南京,出任中央大学(原名东南大学及第四中山大学)地理系主任。次年,又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1928年2月,黄侃离开东北大学,应邀到中央大学任教。两人重逢,喜爱摄影的竺可桢向黄侃送来了二张庐山风景照:“竺藕舫又送庐山摄景二纸来。”(《黄侃日记》1928年9月9日)原来此年7月,黄侃应邀赴庐山讲学。演讲完“国学研究法”之后,黄侃与汪东、竺可桢等四人结伴同游庐山美景,“南见五老峰之背,假竺君远镜窥之(予所携甚小)”(《黄侃日记》1928年7月26日)。相约同行登峰探险,共赏山林岩壑浮岚暖翠之美,足证竺、黄两人交谊不浅。
竺可桢自1918年归国之后,辗转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天津南开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任教。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次年,主持中国气象学会第五届年会,当选为会长。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他的一生注定要与许多不同领域的杰出人物和重要人士相遇、相识、相交往及相周旋。
4.
佛家曾说“功不唐捐”。竺可桢的学术文章固然令人敬佩,他在“立德”、“立功”领域留下的许多业绩——他的道德人格、嘉言懿行以及他倡导的“求是”精神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处世风范,尤其受到了浙大师生与中科院后辈发自肺腑的敬仰,以致有论者称其为“伟人”,并说“竺可桢是本世纪在中国科学家中最值得敬仰的大师,这样的伟大人物100年中也不过7、8个人”(《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120周年文集》第44__45页)。考虑到一个文弱书生在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把个体生命的才华于多个领域发挥到如此极致的境地,笔者亦高度认同这个“伟人”的称呼。
特别令人赞叹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竺可桢于学术研究、行政管理之余,持之以恒地每日撰写极为详尽的日记(早期十多年日记已在抗战时期散失,见《竺可桢传》第298一-299页),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科学技术、人文历史、社会经济等等许多领域——五十多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写下一部罕见的长篇日记,尤为世人所难以企及。
这里暂且说得保守一点,笔者至今已通读过八十多部大陆、港台两岸三地公开出版的晚清民国日记,其中有十多部每一部皆卷帙繁复字数多达几百万之巨,然而如从装帧设计、纸张材质、编校质量以及由学界耆宿、专家俊彦组成的“编辑委员会”所显示的豪华壮观阵容,加之每卷皆附作者大量珍贵历史照片这几个要素作综合考量,据管目所及,海内外中文世界至今尚无一部日记能够超越容量丰富、篇幅之广的《竺可桢日记》。
在我国历史上,人们很早就撰写日记,有源于汉、唐几种说法。宋代王安石曾作《日录》七八十卷,可见规模不小。清代之初日记尤为繁兴,至晚清时期达官显宦、文人雅士作日记者已呈鼎盛之势(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竺可桢日记》无疑是这个日记王国中的古今第一巨无霸,现存16卷一千三百多万字数已超越晚清四大日记(《越缦堂日记》、《缘督庐日记》、《湘绮楼日记》、《翁同和日记》)字数之总量。即此一端,就可称之为:伟哉竺公,非常人也!雄哉竺公,人中龙也!
现存《竺可桢日记》自1936年至1974年,历时将近四十年,犹如一幅万里长江图,烟波浩淼,浪涛汹涌,气象万千,景色诱人——只有从头至尾通览一遍,读者才能看到历史细微处许许多多曾经被遮蔽的隐秘图景,有助于构建近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文化史及思想变迁史。
《竺可桢日记》包含在《竺可桢全集》之中,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整理编辑班子强大,前后得到三个基金会的资助。2004年首先出版1__4卷文集,2005年出版第5卷外文著述,同年开始出版第1卷《日记》,至2011年年底出版第16卷《日记》。前后叠加,至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竺可桢全集》已是煌煌巨著21卷(精装16开),一字排开,气势不凡,可说是新时期繁荣昌盛的国力在出版界的一种体现。第22卷包含补编、年表和人名索引等内容,估计此卷作为压轴之卷于2012年年底出版之时,即是《竺可桢全集》杀青竣工之日。笔者追随《竺可桢日记》出版步伐,历时多年,至今已通读完这一部罕见的日记巨著。
竺可桢一生结交学界人物众多,横跨科学与人文两个领域及多个专业,其中与历史学家陈寅恪之交往尤其令人注目。在当下陈寅恪研究资料几乎已被人“竭泽而渔”、发掘殆尽的情形下,《竺可桢日记》的出版又可为之提供许多鲜为人知的形象姿态、思想线索与历史场景。本书以1949年为一条分水岭,用前后两个部分来论述竺可桢与陈寅恪交往之详情。
用户评价
从图书的装帧和作者的背景来看,我预感这会是一部非常扎实的学术随笔,而不是一本迎合大众口味的“八卦”读物。我更倾向于了解,在那个学术资源极度匮乏的年代,像竺可桢这样的科学家,是如何获取最新的国际前沿信息的,以及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中,哪些是受到时代环境的深刻影响。气象研究是依赖精密仪器和数据模型的,而史学研究则更依赖文献的解读和考据。他们二人的工作范式差异如此之大,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内核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也许是共同的文化担当,也许是对“中国学问”未来走向的焦虑与期盼。这本书的价值,可能就在于揭示了不同学科巨擘在面对时代洪流时,相似的精神底色。
评分我个人的阅读习惯是,喜欢在阅读历史人物传记时,能感受到一种“在场感”。我希望这本书不仅仅是罗列他们交往的年表和事件,而是能够通过细致的细节描写,将读者带回到他们会面的那个场景中去。比如,他们是在哪个图书馆的角落相遇?谈话的内容是关于时局的忧虑,还是学术前沿的讨论?对于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能够通过文字想象出两位泰斗坐而论道的画面,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精神享受。我期待的不是一本干巴巴的学术报告,而是一部充满温度和历史厚重感的“对话录”,哪怕这种对话是隐性的、通过旁人记录间接呈现的也好,它总能帮助我们理解,伟大人物是如何在互相砥砺中,完成他们对时代和后世的责任的。
评分说实话,我对这种跨界名人的交往史题材总是抱有一种既期待又警惕的心态。期待的是能看到大师们“人性化”的一面,毕竟再伟大的成就背后,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警惕的是,如果叙事过于煽情,或者为了凑篇幅而进行不必要的过度解读,那就失去了它作为严肃历史读物的价值。我希望这本书能保持一种克制而精确的笔调,聚焦于他们交往的“实证性”内容。比如,他们是否有共同的师友圈?在涉及国家重大科研或文化决策时,他们是否有过私下的切磋?若能展示出两人在学术困境中相互鼓励的场景,哪怕只是通过书信往来的只言片语来侧面印证,都将极大地丰富我们对他们人格魅力的认知。这种基于事实的描摹,远胜于空泛的赞美。
评分我关注这本书,更多是出于对历史语境下知识分子群体关系的兴趣。陈寅恪先生,那一代史学大家中,我个人认为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他的学识渊博,贯通中西,学贯古今,令人望而生畏。我一直很想了解,像他这样一位深居简出的学者,是如何与外界保持着恰到而有分寸的联系的。特别是不同学科背景的顶尖人物之间的交流,往往能碰撞出意想不到的思想火花。气象学与历史学,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能找到他们思维交汇的那个“点”,那将是极为精彩的剖析。我期待作者能捕捉到那些不经意的对话片段,那些可能改变他们治学路径的只言片语,这些才是构建那个时代知识图景的微观证据,比宏大的叙事更耐人寻味。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吸引了我,那种老照片的质感,配上典雅的字体,让人仿佛能触摸到那个时代的温度。我一直对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们身处乱世,却依然坚守着对学术的纯粹追求,那种风骨令人动容。我尤其好奇竺可桢先生这位气象学大家,是如何在那个物资匮乏、信息闭塞的年代,建立起中国现代气象学的体系的。他那种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以及对自然现象的敏锐洞察力,都是我非常想学习的。这本书若能深入挖掘他工作和生活中的点滴细节,哪怕只是寥寥数语,都会让我受益匪浅。我想看看,一位真正的科学巨擘,他的日常是如何度过的,他的思想是如何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打磨和成型的。那种对真理不懈追寻的过程,远比单纯的学术成果更具感染力。
评分很薄的一本,仰慕大师买的。
评分凑单买的,还不错
评分竺可桢与陈寅恪是大学同班同桌?陈寅恪对华罗庚不满?陈寅恪与竺可桢都认为1962年的天象“五星连珠”与时局女主崛起有关联?
评分由于对先生的钦佩,故买了这本书,想对先生了解多一些
评分很喜欢:..张荣明1.张荣明,他的每一本书几本上都有,这本竺可桢与陈寅恪科学巨擘与史学大师的交往很不错,1.在复旦读书时,竺可桢与陈寅恪不仅是同班,尤为难得的竟是同桌。2.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与陈寅恪的首次晤面,由于竺是管理科学院研究所的领导,陈寅恪坦率地谈到他对华罗庚的不满。3.1962年陈寅恪与竺可桢探讨天象五星连珠与时局女主崛起之关联,可以说是找到了华山论剑的真正高手。4.1966年3月20日,这两位当年同桌共读的双子星座最后一次相晤,一位病卧在榻,一位行色匆匆,自此一别,文革如山洪暴发般汹涌逼来,此生再无相见聚首之日矣。竺可桢与陈寅恪是大学同班同桌陈寅恪对华罗庚不满陈寅恪与竺可桢都认为1962年的天象五星连珠与时局女主崛起有关联著名文史学者张荣明教授,以竺可桢的日记为依据,从中钩沉出竺可桢与陈寅恪的种种交往,及双方对同时代人的评论、对时局的解析。期间的许多故事均为前人所未注意。全书图文并茂,观点故事甚为新奇但又查有实据。1肥胖是因为多吃不运动不断反复的减肥噩梦2008年深秋的一天,一个身形肥胖的年轻女子来到了我的诊所,从外表看就知道她是严重的肥胖症患者,需要减重15公斤。当时29岁的她看起来一副被减肥搞得筋疲力尽的样子,在诊疗过程中,总是不厌其烦地问同一个问题有没有干脆不让身体发胖的方法正如所有因肥胖而苦恼的人一样,她也尝试过很多种减肥方法,只摄取蛋白质的阿金斯()减肥法,只吃一种水果或食物的单一食物减肥法,靠食欲抑制剂减肥的药物疗法等等,从她那里听到的减肥疗法多得不胜枚举。但是,无论哪一种减肥方法都没能让她消除烦恼,尽管其中有一些方法能够在一周内达到减重5公斤的效果,但稍不注意,过一两天就又会恢复到原来的体重,有时,甚至会比原来的体重还要增加几公斤。在谈及自身减肥经历时,她一边叹息一边说应该控制饮食多运动可就是做不到。她觉得是自己的意志不够坚定才使得减肥失败。事实上,通过饮食疗法和运动并行而减肥成功的事例也有不少,因此她的自责也无可厚非。不过,无法抑制食欲和不愿运动而发胖真的只是因为她的意志不坚定吗为什么总是无法抵挡食物的诱惑人们对肥胖最大的误解就是肥胖是多吃不运动造成的,想当然地认为他们都是一些嘴馋、懒惰、疏于自我管理的人。多吃不运动当然会发胖,特别是过量饮食比不运动更会让人发胖,明知过量饮食会发胖,可我们为什么还总是控制不了自己呢是意志不坚定,还是肠胃变大了的缘故其实这些都只是原因之一,无法控制食欲更重要的原因是,食欲并不受人的意识支配,它是一种无意识行为。我们经常认为肚子饿或肚子饱是因为胃空或者胃满所致,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那只是我们大脑的一种感觉,
评分很喜欢:..张荣明1.张荣明,他的每一本书几本上都有,这本竺可桢与陈寅恪科学巨擘与史学大师的交往很不错,1.在复旦读书时,竺可桢与陈寅恪不仅是同班,尤为难得的竟是同桌。2.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与陈寅恪的首次晤面,由于竺是管理科学院研究所的领导,陈寅恪坦率地谈到他对华罗庚的不满。3.1962年陈寅恪与竺可桢探讨天象五星连珠与时局女主崛起之关联,可以说是找到了华山论剑的真正高手。4.1966年3月20日,这两位当年同桌共读的双子星座最后一次相晤,一位病卧在榻,一位行色匆匆,自此一别,文革如山洪暴发般汹涌逼来,此生再无相见聚首之日矣。竺可桢与陈寅恪是大学同班同桌陈寅恪对华罗庚不满陈寅恪与竺可桢都认为1962年的天象五星连珠与时局女主崛起有关联著名文史学者张荣明教授,以竺可桢的日记为依据,从中钩沉出竺可桢与陈寅恪的种种交往,及双方对同时代人的评论、对时局的解析。期间的许多故事均为前人所未注意。全书图文并茂,观点故事甚为新奇但又查有实据。1肥胖是因为多吃不运动不断反复的减肥噩梦2008年深秋的一天,一个身形肥胖的年轻女子来到了我的诊所,从外表看就知道她是严重的肥胖症患者,需要减重15公斤。当时29岁的她看起来一副被减肥搞得筋疲力尽的样子,在诊疗过程中,总是不厌其烦地问同一个问题有没有干脆不让身体发胖的方法正如所有因肥胖而苦恼的人一样,她也尝试过很多种减肥方法,只摄取蛋白质的阿金斯()减肥法,只吃一种水果或食物的单一食物减肥法,靠食欲抑制剂减肥的药物疗法等等,从她那里听到的减肥疗法多得不胜枚举。但是,无论哪一种减肥方法都没能让她消除烦恼,尽管其中有一些方法能够在一周内达到减重5公斤的效果,但稍不注意,过一两天就又会恢复到原来的体重,有时,甚至会比原来的体重还要增加几公斤。在谈及自身减肥经历时,她一边叹息一边说应该控制饮食多运动可就是做不到。她觉得是自己的意志不够坚定才使得减肥失败。事实上,通过饮食疗法和运动并行而减肥成功的事例也有不少,因此她的自责也无可厚非。不过,无法抑制食欲和不愿运动而发胖真的只是因为她的意志不坚定吗为什么总是无法抵挡食物的诱惑人们对肥胖最大的误解就是肥胖是多吃不运动造成的,想当然地认为他们都是一些嘴馋、懒惰、疏于自我管理的人。多吃不运动当然会发胖,特别是过量饮食比不运动更会让人发胖,明知过量饮食会发胖,可我们为什么还总是控制不了自己呢是意志不坚定,还是肠胃变大了的缘故其实这些都只是原因之一,无法控制食欲更重要的原因是,食欲并不受人的意识支配,它是一种无意识行为。我们经常认为肚子饿或肚子饱是因为胃空或者胃满所致,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那只是我们大脑的一种感觉,
评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评分还没看完~ 还可以,和印象里的有一点点区别,可能是我记错了书比我想的要厚很多,就是字有点小,不过挺实惠的,很满意!书非常好,正版的,非常值,快递也给力,必须给好评,就是感觉包装有点简陋啊哈哈~~~不过书很好,看了下内容也都很不错,快递也很给力,东西很好 物流速度也很快,和照片描述的也一样,给个满分吧 下次还会来买!我在网上买的几本书送到了。取书的时候,忽然想起一家小书店,就在我们大院对面的街上,以前我常去,书店的名字毫无记忆,但店里的女老板我很熟,每次需要什么书都先给她打电话说好,晚上散步再去取。我们像朋友一样聊天,她还时常替读者找我签名。可是,自从学会从网上购书后,我再也没去过她那里了,今天忽然想起她,晚上散步到她那里,她要我教她在网上买书,这就是帮她在京东上买了这本书。好了,废话不说。前天看《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恋爱,谈得很不讲究。最常见的表现是吵吵闹闹,哭哭啼啼。当然都有缘由。当然后来彼此相信得到了对方的心之后,就不再吵闹了,转而进入“月中无树水无波”的境界。可是此前,他们吵闹得波涛壮阔不足以形容。尤其第二十八回元春自宫中送端午礼品,独宝钗和宝玉的一样,而第二十九回清虚观打醮,贾母又第一次谈宝玉的婚事,黛玉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致使宝黛二人吵得死去活来,直至惊动了贾母。 贾母抱怨说:“我这老冤家,是哪世里的孽障,偏生遇见了这么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没有一天不叫我你心。真是俗语说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几时我闭了这眼,断了这口气,凭着这两个冤家闹上天去,我眼不见心不烦,也就罢了。偏又不咽这口气。” 据悉,京东已经建立华北、华东、华南、西南、华中、东北六大物流中心,同时在全国超过360座城市建立核心城市配送站。是中国最大的综合网络零售商,是中国电子商务领域最受消费者欢迎和最具有影响力的电子商务网站之一,在线销售家电、数码通讯、电脑、家居百货、服装服饰、母婴、图书、食品、在线旅游等12大类数万个品牌百万种优质商品。选择京东。好了,现在给大家介绍两本好书:《电影学院037?电影语言的语法:电影剪辑的奥秘》编辑推荐:全球畅销三十余年并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被公认为讨论导演、摄影、剪辑等电影影像画面组织技巧方面最详密、实用的经典之作。|从实践出发阐明摄影机位、场面调度、剪辑等电影语言,为“用画面讲故事”奠定基础;百科全书式的工作手册,囊括拍摄中的所有基本设计方案,如对话场面、人物运动,使初学者能够迅速掌握专业方法;近500幅机位图、故事板贯穿全书,帮助读者一目了然地理解电影语言;对大量经典影片的典型段落进行多角度分析,如《西北偏北》、《放大》、《广岛之恋》、《桂河大桥》,深入揭示其中激动人心的奥秘;《致青年电影人的信:电影圈新人的入行锦囊》是中国老一辈电影教育工作者精心挑选的教材,在翻译、审订中投入了巨大的心力,译笔简明、准确、流畅,惠及无数电影人。二、你是否也有错过的挚爱?有些人,没有在一起,也好。如何遇见不要紧,要紧的是,如何告别。《莫失莫忘》并不简单是一本爱情小说,作者将众多社会事件作为故事的时代背景,俨然一部加长版的《倾城之恋》。“莫失莫忘”是贾宝玉那块通灵宝玉上刻的字,代表着一段看似完美实则无终的金玉良缘。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相爱时不离不弃,分开后莫失莫忘”,这句话是秋微对感情的信仰,也是她对善缘的执念。才女作家秋微近几年最费心力写的一本小说,写作过程中由于太过投入,以至揪心痛楚到无法继续,直至完成最后一个字,大哭一场,才得以抽离出这份情感,也算是对自己前一段写作生涯的完美告别。
评分书单狗推荐的,还没有看!?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eaonline.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大百科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