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在中国艺术这里,平凡之物可以成其绚烂,平常之地可显出神圣之光。作者深谙中国艺术品的鉴藏,青铜、玉器、陶瓷、书画,又结合故宫藏品,新的考古发现,颇能得其概要。内容简介
《福开森作品:中国艺术讲演录》语涉中国艺术的一般精神,其后涵盖青铜和玉器、石刻和陶瓷、书法和绘画,视野之开阔,见识之广博,当时的西方汉学界无人能出其右,放在中国艺术研究界也是不遑多让的。《福开森作品:中国艺术讲演录》结合故宫藏品,新的考古发现,以及自己的鉴藏经验,内容翔实生动,非一般浮泛之论可比,特别适合作为中国艺术的入门书。
作者简介
福开森(John C. Ferguson),南京大学与上海交大的创校元老,民国旅华洋人中,中国古物收藏第一人,故宫博物院评审委员会唯一的外国专家,旧上海著名的福开森路(今武康路)即为纪念此公。目录
译者前言第一讲 导论
第二讲 青铜器
第三讲 玉器
第四讲 石器
第五讲 陶瓷
第六讲 书画
第七讲 绘画(一)
第八讲 绘画(二)
精彩书摘
第一讲导论 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北京国立博物馆有着独特的地位。这里收藏着中国最璀璨的艺术珍宝,其建筑的布局和细节,历史深厚的周边环境,以及它的藏品,纯粹是中国特色的。青铜和玉器,绘画和书法,陶和瓷,墨和笔,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即中国人特有的天赋。这个博物馆无须向别国借用早期艺术品来说明其自身发展的直接或间接来源;相反,表现于这些中国有史以来的不同艺术形式中的艺术精神,甚至与这个国家远古的神话和传说传统结合在一起。 中国艺术发端 一个富于艺术气质的民族,阐释自己的艺术并定下自己的价值标准,是其固有的权利。我们自然也想知道,中国艺术给邻国,以及西方学者和艺术批评家,带去了什么影响。不过,此领域里已有的这些观点,只有建立在浩瀚的中国艺术文献中举世公认的经典之上,才能成为定论。将中国艺术与其他古代民族如希腊、罗马,或埃及的艺术相比较,在此基础上判定中国艺术的价值并给予它相应的重视—与它此前所确定的相对价值相适应—是非常正确的。这是艺术的比较研究。 但是在中国艺术的内部研究中国艺术,则它自己的标准必定具有优先权。这个新领域的外来探索者,千万不要带着由自己国人所完善的现成罗盘,因为不同的气流和水流会扭曲它的指针,使它失效。必须在你所研究的国度里获得你的罗盘,唯有如此,罗盘才能得到充分的调整和校正。千万别想当然地以为,对你来说是新的东西,对土生土长的该国人来说也是未知或未加研究的,特别是你所面对的这个民族,在悠久历史中,一直致力于文化上的追求。也许与中国人相比,你的观察方法更科学更精确,但是作为一个探索者,首先应该留意比你更早,因而更有机会观察那些事实的先人的分类和解读。 外国学者对中国艺术感兴趣自有其道理,因为中国艺术完全是民族的,表现了古老的华夏民族的理想和精神。我们很难把中国艺术视为亚洲艺术的一部分,因为民族交流所引起的互动,对中国艺术的发展无太大影响。你不能像使用“欧洲艺术”一词那样,随意使用“亚洲艺术”一词。欧洲的所有艺术,在一个可信的历史时期内,都可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来源:希腊和罗马。然而在亚洲,最早的历史记载会把我们带回到数种不同的文明,那时它们各自就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足以形成不同类型。我们若要追寻它们的来源或相互关系,只能借助于猜想。 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即中国至少有一个文明系统和一种艺术,发源于它自己的疆域之内。我们无须借助印度、日本或波斯艺术的知识,就可以理解中国艺术—不管侧光的照射多么有意义。在研究中国艺术时,唯一精确的观察点,是站在中国自身文化发展的中心。 中国文化之精神 在中国,艺术是文化的表达。希腊人所谓的paideia,罗马人所谓的humanitas,中国人称之为“学”或“问”,意思是通过精神和道德的修养而获得的风度和品味上的提升。中国人从未低估技术的价值,但从不把手工的灵巧当作艺术的核心法则。“遵从文化”向来是艺术表达的第一要素,而文化是高贵的民族理想的产物。技术向来是艺匠之作的信用证,不过艺匠作品已经被拒于艺术的殿堂之外。只有那些与文化精神相一致,对文化精神有所贡献的作品,才能在艺术殿堂占有一席之地—不管那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如何。 中国人从未想过通过传授某种高明的画法来培养画家;他们向来认为,在训练一双专业的手之前,先须用精神文化充实其灵魂。有时,比如在青铜器和玉器的制作中,就连艺术家的个性,也完全屈从于那个至高无上的要求,即,作品须符合家国的理想。一个艺术家最了不起之处,往往是他成功抹掉了个性,从而使观者首先想到的不是艺术家的技能,而是作品的美丽、优雅、高贵,以及该作品在其民族的文化积累中的位置。 那决定了中国艺术之生命的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是对仪礼,也即对家庭礼仪和氏族礼仪的热爱。忠君,敬父母和长者,这两个原则是立家和立国之本。我们所知中国最早的艺术品,家族或氏族聚会所用的青铜器,即为此而造。所有这些场合,典礼的仪则都制定得纤悉备至。据商代(前1766-前1122)文献如《尚书》所载,典礼上对国君、臣子以及朝廷的所有相关人等,都有周致的仪则规定。这些仪则在周代(前1122-前255)固定下来,它们如此稳固,至今还支配着中国人的典礼和祭祀。1915年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时所采用的仪礼,包括参加天坛祭礼的服饰,即以周礼为基础。 对仪礼的热忱甚至投射到了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三皇指天皇、地皇、人皇三位神祇,皆受极高的敬重。五帝则有着奇幻的名字,如筑巢的有巢氏,生火的燧人氏。这些想象的人物,是中国人为了解释最初的文字记载中所体现的文化而虚构的。他们显然是后人生造的,其意义仅在于表现中国人在历史开端时期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我们感兴趣的是三皇五帝对于了解礼仪有何启示—我们发现,这些礼仪在最初的正史中就有充分的表现,说明这些礼仪必定在古代就很好地建立起来了。但是对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解释此现象的唯一途径是虚构神话和传说性质的“创造说”。 九鼎是文献中提到的最早铜器。据说夏禹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州牧进献青铜合铸此鼎。《左氏春秋传》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周德修明),鼎迁于周……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我们关于九鼎的所在地及其使用的全部知识,都来于这个记述。关于此记述的真实性,我完全赞同理雅各(1815-1897)、夏德(1845-1927)。禹铸九鼎的说法,可以存疑,甚至可以彻底推翻,但是九鼎在夏商周的使用,确实已经成熟地建立起来了。在国家最庄重的典礼上,九鼎是主器,象征着对帝国权力的掌握。(图1-1) 家庭生活也精心地仪礼化了。由早期青铜器上的铭文可以知道,有时它们是子献给父的,也许是祝寿;也用于向祖先献祭,盛祭品或祭酒。战功和某个家族成员获得的特殊荣誉,也记录在这些器皿的铭文中,而早期文献中所提到的周致的家庭礼仪,亦由此得到印证。家族的地位越高,礼仪越周密。天子的日常活动皆有详细安排,其礼仪是如此繁复,假如他忠实履行自己职责的话,可能就没有任何闲暇的时间了。 与仪礼相联系的是卜筮。人们希望通过它了解天意,并且预知一生境遇。卜筮的工具有龟甲、兽骨、蓍草。以龟甲或兽骨占者,置甲或骨于火上灼烧,产生裂纹,占者就从那裂纹的图案中识出征兆。以蓍草筮者,则观察蓍草摆动的方向。 卜筮的出现一定很早,在最初的文字记载中就有它的踪迹。据《大禹谟》,舜尝掌占卜之事,并曾告诫禹,即使是吉兆,也不能重占(“龟筮协从,卜不习吉”)。商朝掌卜筮之事者为盘庚,而周朝的王宫里,则有一大堆卜人。在政府官员中,占卜官的地位很高,类似于恺撒大帝之后的罗马—罗马十六名占兆官的排位紧跟在大祭司团之后。 识读占卜的征兆、符号的排列,成为饱学之士悉心钻研的课题,其最大的知识宝库即是《易》。这本书极难理解,但是以它对中国人生活和思想的影响,却是研究中国艺术之起源及其灵感所不能忽视的最重要文本之一。它与老子所创建的道家的理论和实践,有着难分难解的联系。 纹饰与龙凤瑞兽 仪礼和天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艺术首先从中发展起来。想象之物和审美之物的创造,亦有其存在的空间,但总是指向它们在仪礼或卜筮上的功能。然而从一开始,艺术就试图挣脱包围着它的文化生活的约束。这挣扎的第一个重要成果,是九鼎上的“异像”纹饰—该纹饰的目的是为教导人们认识山川之灵,以免被它们的邪恶力量所伤。接着出现了装饰青铜器和玉器的凤、龙、云雷、牛头怪兽、饕餮等图像。 与此相伴的,是表意文字的出现—它后来发展成为书面语言。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起初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两者都用于装饰,其艺术性质在于它们是想象之作,而不是追摹已知之物。表意和表物的区别,表述在圆和方两个几何术语之中。《易经》说,圆(即图)出于河,方(即书)出于洛(图1-2)。“圆(图)”指一组据说是神话中的伏羲在龙马背上发现的符号,伏羲还由此衍演出八卦。这些符号呈圆环状,图画(地图绘制)、装饰以及想象性设计的原理皆发源于此。“方”则由大禹在龟甲上发现的图案发展而来—其时大禹正在实施他伟大的治水蓝图。据说那些图案是表意文字的原型。那是一组从一至九顺序排列的数字,大禹据此安排自己治水工程的九个部分或曰九州。 据说每个数字的每一部分都是一个表意字,关于这些表意字的数目,古代学者有许多讨论。《汉书》曾提到禹在龟甲上发现文字一事,但是《汉书》没有给出文字的数目。近年在河南省发现了类似的甲骨,证实史前确有使用刻着文字的龟甲之事。我们不必进而也相信关于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之来源的那些离奇解释,但必须知道,象形文字与表意文字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出现得如此之早,以至早期文献不得不为它们的初次出现提供解释。即是说,关于其起源的神话故事应该抛弃,但是我们必须接受其在历史的黎明时期即已存在的事实。因此,中国艺术的根深扎在那样一个时代—家庭和部族的卜筮与仪礼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时代。 这种交织的印迹,可以在发明创造、科学、文学、艺术的结合上见到。艺术后来称为“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这当中,仅礼、乐、书符合我们近代的艺术概念。“礼”恰如我们美术中的舞蹈,“书”相当于我们的画(drawing)。我们西方的美术(finearts),由绘(painting)、画(drawing)、建筑、雕塑构成,外加诗歌、音乐、舞蹈、悲剧。而中国古代的“艺”,除了礼、乐、书三种之外,建筑、雕塑等都被遗略了,代之以射、御、数(计算)。“射”的意义不仅在于射击的“中的”技巧,它还配合着优雅的身体动作,以便作为君子(绅士)的一项训练。这就把“射”联系于礼仪性的舞了。“御”之艺则为战车及其配置的装饰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所有的装饰都必须符合其出现的场合以及车主人的身份。这只能由具有艺术精神的人来完成。“数”起初与土地丈量和地图绘制有关。《礼记》有一节说,“一国的财富可由其领土的大小来计算”(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考虑到“数”是六艺之一,我认为此节的含义是:领土的总量可以由经调查而绘成的地图计算出来。由此,“数”确实是测量之义。惟有如此,才能解释何以计算过程中可以有艺术表现。 近代以来,一个新名词“美术”被引入中文,用来表述“finearts”观念。如今这个词已经被普遍接受了。它遵从我们西方的观念,将音乐、诗歌、雕塑、建筑与绘画一道作为“美术”。这当然是个很有用的术语,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一个用于解读西方艺术的近代词汇,与古代中国人的观念多少有些差异。 中国艺术与古希腊罗马艺术的根本差异,可以从它们文化类型的鲜明对比中见出。中国人的理想,是孝亲忠君。因此,他们把礼当作人伦关系的规则,并以为这符合至高无上的天意;也因此,他们视占卜为一种自然的欲望,以图了解未来之事如何影响人伦关系。古希腊和罗马的理想,是政治自由,以及个体的人在天地间的重要性。一言以蔽之,早期中国文明以“君”为中心,而古希腊罗马文明则以“人”为中心。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即:中国艺术具有本土的性质,它只可能起源于扎根中国土壤的文化,而不可能起源于别处的文化。 至于它与别国艺术的类似之处,则可以由各民族所共有的一般性质得到解释。比如对古代游牧民族来说,繁星点点的夜幕呈现为具有动物之形的黄道十二宫,如金牛、狮子、天蝎等,对作为农耕民族的古代中国人来说,掌控他们未来的自然力量也转化为动物之形。在夏天,雷雨前的云呈现为龙形,有硕大的头,开张的爪,长长的尾。这是给土地带来生产力的风雨之灵。因此,龙便成为四种瑞兽之一—另外三种瑞兽是麒麟、凤凰、龟。麒麟、凤凰对应春天,象征生命的到来,龟和龙对应带来丰收的夏雨。这四种瑞兽之形,皆是最先用于青铜器装饰的图案,而且都倾向于激起好的念头。 我不同意夏德的观点。他认为“龙凤之名虽见于最古老的文献,但早期艺术品中的龙凤之形却大异于后期艺术家所创造的精美的龙凤图像”。我也不认同沙晼(1865-1918)所说,“这组不可思议的象征性形象(如龙和凤),也许根本不是中国的,一开始就不是,而且无论如何不会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古老。汉代之前,我找不到任何类似凤的东西”。这些观点与中国考古方面最优秀的权威完全不同调。在卷五中,阮元(1764-1849)提到了一件酒器,爵,其上镌有一字,字形为一只栖于树上的凤。此器现归潍县陈氏。还是在卷五,薛尚功(南宋)提到了一只觚,其上有一象形字,字形为一条龙(图1-3)。薛尚功定其时代为商。此器近年归汉阳叶氏。我曾见过吴重羲定为商代的一个器皿,其上装饰着一只刻画精细、线条优美的凤。(图1-4) 在装饰领域,与这些瑞兽相联系的,是另一些模样狰狞,带有凶兆性质的生灵,它们是为了惩邪诫恶。其中最常见的即是饕餮—夏德承认这是中国人的发明。饕餮是最早的装饰图案之一。它双眼爆出,面相狰狞,警告世人切勿贪婪,暴饮暴食(图1-5)。早期青铜器上用于装饰目的的那些生灵,无论是瑞兽还是凶兽,彻头彻尾是中国人想象的产物,其基础是古代中国所流行的生活方式。 文化遗迹缺失 除了将我们带回商代文化的青铜器和玉器,以及可能更早一些的甲骨文,没有其他实物可以证明《书经》(即《尚书》)中的记述。关于尧和舜,以及大禹治水的记录,目前我们只能看作是后人的追想—其目的是从某种更早的源头推导出他们所知的文明,当然,那源头是他们所乐于认同的。公元280年左右发现的“竹书”,只是印证了司马迁《史记》里的记录,几乎没有增加任何内容。那些湮灭了的遗迹必定与其他古文明所拥有的遗迹同时,甚或更早。但与埃及和亚述的古城遗迹相比,中国缺少纪念碑式的文化遗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与埃及和亚述相比,中国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不利于遗迹保存。 汉代之前的石碑,没有一件是可靠的。贵州永宁有一块无纪年的古碑,被定为周代之物,但是很可疑。另一块在江苏丹阳的古碑,上有篆字铭文,据说最初是孔子所书。此碑正面有《记》,说篆文是公元799年(唐大历年间)重刻,但是现存文献,无法证实《记》中宣称所刻篆文为孔子所书一事的真实性。直隶赞皇也有一碑,被认为是周穆王所写,其他如河南汲县、直隶大兴的一些古碑也被归于周代。此外还有一些秦朝的砖,这些秦砖的真实性似乎是不必怀疑的。广为人知的《访碑录》中,也有四通碑系于秦朝。其中最著名的是泰山顶上的那一通,习称“无字碑”,据说是秦始皇所立;其他三通分别在山东诸城,陕西西安和浙江会稽。有一通汉碑,署年公元前143年,但是对于它的真实性,有许多争论。最早的可靠的石碑,在孔子故乡山东曲阜,署五凤二年(即公元前56年)六月。坦率地说,对于研究中国艺术考古的人来说,这是颇令人失望的—我们无法找到比中国学者目前所知更早的石刻。 最早的石质历史遗物是石鼓(图1-6),如今安置在北平孔庙大成门左右的两庑下。石鼓是七世纪(隋唐时期)在陕西凤翔发现的,九世纪时安置于凤翔的孔庙。宋徽宗将它们移到河南开封,并用黄金填注石鼓上的文字。金人攻占汴梁(开封)后,将石鼓运往北京,1307年郭守敬(1231-1316)将它们安放在现今所在的地方。石鼓共十个,每个鼓上刻着一首/篇颂。这些颂大抵是为纪念周王巡狩岐山—即在掘出石鼓的凤翔境内。颂描述了为这次光辉的军事检验而作的精心准备,比如平整道路,拓深河道。没有内证能够帮助我们确定这些石鼓的年代,但是中国学者一致认为它们属于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前782),对此我完全赞同。布谢尔(1844-1908)倾向于把它们放到更早些的成王时期(公元前1115-前1079),而沙晼则将它们系于公元前300年前后的某个秦国国王。石鼓的唯一装饰是它上面所刻的字,而石鼓的艺术性则在于其形状。这些石鼓主要对考古学家和文献学家有价值,但是中国人视其为民族艺术的一部分。 修筑长城是一件无比浩大的工程。修筑时间跨越了战国时的秦、赵、燕,一直到把它加以延长的秦始皇。然而我的印象中,没见过它被用作任何早期艺术品的主题,无论石刻,玉器,还是绘画。即便陶器中保存下来的汉代望楼,也是在陕西所发现的那种望楼,而不是长城上的那种望楼。艺术中有许多指向狩猎之旅和山路行军的线索,但是没有一个指向长城本身。长城完全被当作一个军事要塞,而从不被当作人民精神或天赋的产物。 早期建筑却不是这样—它们已经在民族的艺术发展中赢得了一个位置。据说,神话般的黄帝(公元前27世纪)教民制砖作室,“筑城邑,造五城”。在周朝,“王宫是一个巨大的围笼,被高高的土墙或砖墙包围着,围墙里面有王、后、众妃及其仆人的起居室,大臣的办公所;朝会的殿,庙;宫廷所用的丝麻织品商店;保存帝国档案、历史文献、珠宝等国家和皇帝所拥有的珍宝的库房;存放生活必需品的仓库。即是说,它是首都里一个用围墙围起来的小城,是皇帝、皇室及政府专用的。除非公务的需要,皇帝很少走出围墙。” 如沙晼在《司马迁Ⅱ》第174页所解释的,阿房宫是秦始皇(公元前221-前209)所建,位于陕西西安。这是一座雄伟壮丽的建筑,其形象经常出现在画里和瓷器上,就像诗里所称颂的那样。据《史记》,阿房宫坐落于上林苑渭水南岸,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殿中可以坐一万人。早期著名的宫殿还有长安附近的未央宫,汉初萧何(?-公元前193)所建。此外还有甘泉宫。这三座宫殿在诗画里很有名。有一幅名画是宋代李唐(约1100年前后)所作,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壮丽的阿房宫印象。这几座宫殿奠定了后世宫殿的模式,其主要特点还可以在今天的北京故宫身上看到。可惜的是,这些宫殿没有一座能够经受住时间的侵蚀而幸存下来。因此,我们必须相信文献的记载,承认后世的宫殿与它们相似。(图1-7) 古代艺术遗迹的缺失,从未令中国的艺术批评家感到不安—早期实物会消亡,但是将那相同的艺术精神,代代传承,是中国人的一种天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商周时期盛行的那些艺术主题,也同样激动着明清时期各类艺术家的心。中国人从来不担心临摹/复制,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从来不是一种依样画葫芦的奴性行为。临摹者并不惟谨惟细地追随临摹对象,因此每一次临摹都会体现出临摹者的个性,即使他们都遵循忠于原作的那个总原则,结果也是如此。 在中国人看来,这种方法既是对民族意识的颂扬,也是对珍贵传统的维护。早期青铜器的器型复现于陶器,然后又复现于瓷器;早期铸器上粗简的龙凤像,在绘画中变美了,可见每一代人都从同一个永恒不坠的资源中汲取着艺术灵感。这常常给外国人一种单调的印象,就像布谢尔提及中国建筑时所说的那样。然而从如此有限的资源,孕育发展出如此多样,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变化,也着实让人敬佩不已。在保持艺术精神的连续性方面,中国人做得比其他任何民族都好,他们那连绵不断的传承,已经维持了四千年。(图1-8)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远在中国与外族发生较多的交往之前,那时中国的疆域还偏于一隅,即现今它的西北部,其艺术母题已经稳定下来了。在本演讲中,企图追寻中国人的种族起源,自然没有什么意义。拉克伯里(1844-1894)曾努力证明中国人是巴克族人,在巴族首领奈亨台的带领下,穿过突厥斯坦,沿喀什河来到中国西北—中国的发源地。这样,他就给了中国文化一个巴比伦血统。夏德已经从文献基础的方面有力地驳斥了拉克伯里的论点。我则必须从艺术主题的方面提供证据,证明拉克伯里理论的不可靠。他说,中国人系于其早期教化者名下的艺术列表,往往是早期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奇怪的杂合。 外来艺术影响 这些早期的艺术和传统,在中国和其周边民族开始有交流之前,就已经牢固建立起来了,这使得它们不仅能够在交流中存活下来,而且能够掌控、支配外来的影响。 公元前五世纪有一个经由蜀国(今四川省)连接秦国(今陕西省)和印度的陆路通道,然而我们知道,那时中国青铜器和玉器的制作,以及至今仍然支配着中国艺术家心灵的那些观念,已经发展起来了。此后,中国和外部世界来往频密。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旨出使都城在奥斯苏克河的月氏国。十三年间,他穿越了东突厥斯坦、费尔干纳(汉称大宛)、巴克特里亚(汉称大夏)、和田,带回许多新作物,如葡萄以及苜蓿。他还记下了所访国家的物产和习俗。 佛教在公元67年由汉明帝以官方形式引入中国。他派出的使者从印度带回了两位高僧,同时也以白马驮载来了他们的巴利文书佛经、佛像,还有他们的习俗。洛阳东边的白马寺,就是为了铭记白马驮经之功而敕建。这座寺院曾经数度重建,至今犹存。司马迁(公元前85年去世)在《史记》中记录了中国和突厥、南夷、大宛的联系。公元97年,班超带领一支军队前往安提俄克-马尔吉亚那;他命令部将甘英从波斯湾乘船前往罗马—那时罗马刚刚为中国所知。这次探险并未成行。又过了一个世纪,罗马商人才发现了前往交趾支那的路,不久又发现了前往广州的路。穿越帕提亚(即安息)、撒马尔罕,到达罗马、北印度的陆上贸易之路也重开了,结果在汉之后的南北分裂时期,有些小国被突厥人统治了。魏和北魏皆定都平城(大同),直到北魏中期孝文帝迁都洛阳。这两个朝代都在其艺术品中反映出突厥斯坦和键陀罗的影响。 大唐帝国几乎将所有邻国置于其控制之下,西北疆的许多小国都向中国寻求保护,以抵御穆罕默德(伊斯兰)势力的壮大。阿拉伯人的船抵达广州,基督教(景教)传教士、犹太人、摩尼教由陆路来到大唐帝国,佛教的中心也由印度转移到了中国。在这个百业兴旺的盛世,艺术繁荣起来。这一时期,外来影响强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然而中国艺术继续表现出对其早期固有传统的坚持,拒绝侵蚀。从外部世界引进的艺术母题,服从中国原则的支配,而且中国人在应用这些母题时,与已有的标准或规则融合无间。 蒙古忽必烈于1280年建立的元朝,重建了宋代陷于分裂的帝国,但是在艺术方面,则将艺术的精神从保守派的僵硬拘泥中解放出来。其结果是自由精神的迅速复兴—我们在唐代曾经见过这种自由。蒙古人统治过的疆域如此巨大,甚至出现了波斯和中国之间互换工匠的现象。波斯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工匠的影响,但是波斯工匠却没有在中国留下长久的印记。 明代甚少或者简直就没有外来的影响。过去的一百年里,西方的影响也没有能够足够深地渗入中国人的内心生活从而控制或影响其艺术。固守并延续一种艺术生命,将之系于其最初的民族传统,中国是唯一的活例。中国艺术频繁受到外来影响,但从来没有背离其独有风格。相反,它总是吸收这些影响,使之为己所用。它借用了外来的装饰形式,甚至可能借用了外来的技法,却将之置于自己的原则和规范之下。 因此,我们必须把中国作为一个艺术实体来研究。现今在中国支配着评论和创作的这些原理和规则,正是来自其民族生命最初的那些原理和规则。从作品来看,中国艺术如今确实衰落了。然而从其对原则的坚守来看,它的繁荣之力一如其黄金时代—唐朝。我们在任何一个文化人身上都能够看到它,而且它努力在每个新起的收藏家身上发生作用。它的无往不在甚至没有因近代教育的到来而受到干扰。 据中国人的习惯,艺术品分为金石(青铜、石刻、陶瓷)和书画(书法、绘画)两类,大致可以视为造型艺术和图形艺术两类。金石类是艺术和考古不可分离的结合,换言之,它是考古艺术或艺术考古。书画类是纯粹的美术。下面的讲演,即在这两个部类之下讨论中国艺术。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作品集简直就是一场精神上的饕餮盛宴,作者的博学和对艺术的热爱溢于言表。我发现,他不仅仅是在讲解艺术技法,更是在传递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种充满东方哲学意境和审美情趣的视角。书中的有些段落,读起来简直就像在欣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句式长短错落有致,充满了音乐感。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深夜里读到关于某位山水画家的章节,作者描述的意境之幽远,让我几乎能闻到墨香,听到松涛声。这种强烈的画面感和听觉体验,是很多纯理论书籍无法给予的。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成功地搭建了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让现代读者得以直接与古人的创造力对话。它不是教你如何画画,而是教你如何去“理解”艺术背后的“道”,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教育的精髓所在。
评分我必须承认,这本书的学术门槛不低,但阅读的体验却是极其愉悦和充实的。作者的结构安排非常巧妙,他没有采用简单的时间线索,而是根据艺术主题和精神内核来进行分篇论述,这使得不同时期的艺术元素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下进行比较和对话。我特别欣赏他对“地域性”与“时代性”之间相互作用的探讨,这让原本零散的艺术史知识点被整合进一个有机的整体中。这本书让我深刻体会到,中国艺术的伟大,并非偶然,而是特定历史、哲学、社会环境共同孕育出的必然产物。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遗产的深度解读报告,读完之后,我对“国风”二字的理解也变得更加立体和深刻。这是一本能真正提升个人文化素养的书籍,值得所有对中国文化有敬意的人细细品味。
评分这本厚厚的书拿到手里,沉甸甸的,光是油墨的香味就让人感到一股浓郁的学术气息。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翻到它的,原本对这个领域了解不多,但作者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魔力,仿佛能把我拉回到那个遥远的时代,亲眼目睹那些伟大的艺术创作过程。他不是那种枯燥地堆砌年代和技法,而是将艺术品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文人的思想情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读这本书,就像是进行了一场深入的文化寻根之旅,让我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理解从表面的“好看”提升到了灵魂深处的“为什么”。尤其是一些关于早期绘画风格演变的论述,逻辑清晰,论据扎实,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洞察力。我特别喜欢其中穿插的一些小故事,它们不仅让原本严肃的学术内容变得生动有趣,更让那些历史上的艺术家形象立体了起来,不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符号。这本书的排版和装帧也十分考究,让人在阅读的同时,也享受着一种视觉上的愉悦。
评分说实话,一开始翻开这本书,我有点被它的密度吓到了。这哪里是“讲演录”啊,简直就是一部微型的艺术史百科全书。我通常阅读比较偏爱轻松愉快的题材,但这本书却有着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引力。作者的叙事节奏把握得极好,时而如涓涓细流般娓娓道来,细致入微地剖析某一幅作品的笔触和意境;时而又如洪钟大吕般,对整个艺术思潮的走向进行宏观的判断和总结。我发现,很多我过去似是而非的认知,在这本书里得到了系统性的修正和补充。它迫使我停下来,反复琢磨那些看似寻常的艺术现象背后的复杂文化密码。我尤其欣赏作者在论述中展现出的那种批判性思维,他从不盲目崇拜经典,而是敢于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见解,这种探索精神本身就极具感染力。看完一部分,我常常需要合上书本,走到窗前,或者去美术馆转一圈,让书中的思想与现实的视觉经验碰撞、融合,那种“醍醐灌顶”的感觉,真是无与伦比。
评分这本书给我的最大感受是“沉浸感”。它不是那种走马观花的介绍,而是真正深入到了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地带。作者的文笔洗练而富有韵味,即便涉及晦涩的理论概念,也能用非常贴近生活的比喻来加以阐释,使得即便是初学者也能轻松入门,同时又不失专业深度。我尤其对其中关于“士人趣味”如何渗透到各个艺术门类的论述印象深刻。这种从哲学、文学到视觉艺术的贯通,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让我看到了中国艺术的生命力所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仿佛站在作者的身旁,听他慷慨激昂地向我们这些后辈揭示前辈留下的智慧宝藏。每一次翻阅,都有新的领悟,它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当代人对传统美学的疏离与迷失。这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时常翻阅的案头书,每一次重读都会带来不同的感悟,它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凸显。
评分中国艺术讲演录值得一看。
评分毫不犹豫的买下了,京东速度果然非常快的,从配货到送货也很具体,快递非常好,很快收到书了。书的包装非常好,没有拆开过,非常新,可以说无论自己阅读家人阅读,收藏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的说,特别精美;各种十分美好虽然看着书本看着相对简单,但也不遑多让,塑封都很完整封面和封底的设计、绘图都十分好画让我觉得十分细腻具有收藏价值。书的封套非常精致推荐大家购买。 打开书本,书装帧精美,纸张很干净,文字排版看起来非常舒服非常的惊喜,让人看得欲罢不能,每每捧起这本书的时候 似乎能够感觉到作者毫无保留的把作品呈现在我面前。
评分好评,送货速度快,东西好,正品
评分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深刻影响着艺术精神的后续发展,并最终成为一条延续不断的历史长河。所以福开森也惊叹这种艺术精神源流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认为“固守并延续一种艺术生命,将之系于其最初的民族传统,中国是唯一的活例”。并且,中国人对艺术精神传承的看重,远远高于艺术品本身,在福开森看来,这无疑是“中国人的一种天赋”,因为这种天赋,以至于“商州时期盛行的那些艺术主题,也同样激动着明清时期各类艺术家的心”。他指出,中西方艺术难以用同一个术语体系来阐释,中国是独特,中国艺术上有深深的民族文化烙印。在将中国艺术与古希腊罗马艺术进行比较时,他更清晰地发现了中国艺术所具有的鲜明本土性质,强调“它只可能起源于扎根中国土壤的文化,而不可能起源于别处的文化”,而那些与其他地域、民族的艺术所具有的相似之处,则是由各民族艺术所共有的一般性质使然,属于艺术的共通属性。
评分很棒
评分一次性购买了*元的书,质量都不错,,先晒一批到货的,值得购买
评分好书,最近天气好正好看书
评分吹嘘自己有知识的人,等于在宣扬自己的无知。
评分比我想象的内容少,也值得一读吧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eaonline.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大百科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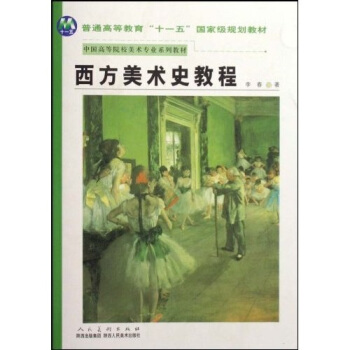






![HBO官方指南 权力的游戏:幕后及艺术设定(卷2第三、四季精装) [Inside HBO's Game of Thrones: Season 3 & 4]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697035/55656f2dNe7cc0e56.jpg)




![《霍比特人》的艺术 [The Art of The Hobbit]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393147/543b90cbN5c26c5e4.jpg)


![性与艺术 [How To Read Erotic Art]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902353/5707cdbaN8dad2b78.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