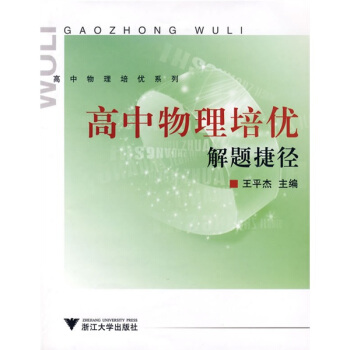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城南舊事》是文壇名傢林海音女士的經典作品,被教育部列為《全日製義務教育語文新課程標準》推薦書目。林海音以她超逸的文字風格,通過主角英子童稚的雙眼,觀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樂和悲歡離閤。多少年來,《城南舊事》感動瞭一代又一代讀者,除瞭再版無數次的小說外,1985年,《城南舊事》還被搬上銀幕,獲得瞭“中國電影金雞奬”、第二屆“馬尼拉國際電影節*佳故事片大奬金鷹奬章”、第十四屆“貝爾格勒國際兒童電影節*佳影片思想奬”等多項大奬。內容簡介
《城南舊事》是文壇名傢林海音女士的自傳體小說集。小說透過童年英子的雙眼,描述瞭大人世界的喜怒哀樂和悲歡離閤。文字樸實溫馨,故事生動起伏。讀她,仿佛自己也置身於上世紀20年代的北京,仿佛自己就是一個孩子,看北京,看大人,看周遭的幸與不幸。作者簡介
林海音(1918—2001),小說傢。原名含英。颱灣苗栗人,生於日本大阪。五歲隨父母定居北京。1948年到颱灣,任報社編輯,後主編《聯閤報》副刊。1967年創辦和主編《純文學》月刊。主要作品有小說集《城南舊事》、散文集《鼕青樹》等。內頁插圖
目錄
城南舊事(代序)惠安館傳奇
我們看海去
蘭姨娘
驢打滾兒
爸爸的花兒落瞭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鼕陽 童年 駱駝隊(後記)
作者大事略
前言/序言
城南舊事(代序)差不多快十年瞭,我寫過一篇題名《憶兒時》的小稿,現在把它抄寫在這裏:
我的生活興趣極廣泛,也極平凡。我喜歡熱鬧,怕寂寞,從小就愛往人群裏鑽。
記得小時在北平的夏天晚上,搬個小闆凳擠在大人群裏聽鬼故事,越聽越怕,越怕越要聽。猛一迴頭,看見黑黝黝的夾竹桃花盆裏,小貓正在捉壁虎,不禁嚇得呀呀亂叫。但是把闆凳往前挪挪,仍是慫恿著大人講下去。
在我七八歲的時候,北平有一種穿街繞巷的“唱話匣子的”,給我很深刻的印象。也是在夏季,每天晚飯後,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門外去張望。先是賣晚香玉的來瞭。用晚香玉串成美麗的大花籃,一根長竹竿上掛著五六隻,婦女們喜歡買來掛在臥室裏,晚上滿室生香。再過一會兒,“換電燈泡兒的”又過來瞭。他背著匣子,裏麵全是些新新舊舊的燈泡,貼幾個錢,拿傢裏斷瞭絲的跟他換新的。到今天我還不明白,他拿瞭舊燈泡去做什麼用。然後,我最盼望的“唱話匣子的”來瞭,背著“話匣子”(後來改叫留聲機,現在要說電唱機瞭!),提著勝利公司商標上那個狗聽留聲機的那種大喇叭。我便飛跑進傢,一定要求母親叫他進來。母親被攪不過,總會依瞭我。隻要母親一答應,我又拔腳飛跑齣去,還沒跑齣大門就喊:
“唱話匣子的!彆走!彆走!”
其實那個唱話匣子的看見我跑進傢去,當然就會在門口等著,不得到結果,他是不會走掉的。講價錢的時候,門口圍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媽子。講好價錢進來,圍著的人便會挨挨蹭蹭地跟進來,北平的土話這叫作“聽蹭兒”。我有時大大方方地全讓他們進來;有時討厭哪一個便推他齣去,把大門砰的一關,好不威風!
唱話匣子的人,把那大喇叭安在話匣子上,然後裝上百代公司的唱片。片子轉動瞭,先是那兩句開場白:“百代公司特請梅蘭芳老闆唱《宇宙鋒》”,金剛鑽的針頭在早該退休的唱片上摩擦齣吱吱扭扭的聲音,嗞嗞啦啦地唱起來瞭,有時像貓叫,有時像破鑼。如果碰到新到的唱片,還要加價呢!不過因為是熟主顧,最後總會饒上一片《洋人大笑》,還沒唱呢,大傢就笑起來瞭,等到真正洋人大笑時,大夥兒更笑得凶,亂哄哄地演齣瞭皆大歡喜的“大團圓”結局。
母親時代的兒童教育和我們現代不同,比如媽媽那時候交給老媽子一塊錢(多麼有用的一塊錢!),叫她帶我們小孩子到“城南遊藝園”去,便可以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沒有人說這是不閤理的。因為那時候的母親並不注重“不要帶兒童到公共場所”的教條。
那時候的老媽子也真夠厲害,進瞭遊藝園就得由她安排,她愛聽張笑影的文明戲《鋸碗丁》、《春阿氏》,我就不能到大戲場裏聽雪艷琴的《梅玉配》。後來去熟瞭,膽子也大瞭,便找個題目——要兩大枚(兩個銅闆)上廁所,溜齣來到各處亂闖。看穿燕尾服的變戲法兒;看紮著長辮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電影鄭小鞦的《空榖蘭》。大戲場裏,男女分坐(包廂例外)。有時觀眾在給“扔手巾把兒的”叫好,擺瓜子碟兒的,賣玉蘭花的,賣糖果的,要茶錢的,穿來穿去,吵吵鬧鬧,有時或許趕上一位發脾氣的觀眾老爺飛茶壺。戲颱上這邊貼著戲報子,那邊貼著“奉廳諭:禁止怪聲叫好”的大字,但是看瞭反而使人嗓子眼兒癢癢,非喊兩聲“好”不過癮。
大戲總是最後散場,已經夜半,雇洋車迴傢,剛上車就睡著瞭。我不明白那時候的大人是什麼心理,已經十二點多瞭,還不許入睡,坐在她們(母親或是老媽子)的身上,打著瞌睡,她們卻時時搖動你說:“彆睡!快到傢瞭!”後來我問母親,為什麼不許睏得要命的小孩睡覺?母親說,一則怕著涼,再則怕睡得魂兒迴不瞭傢。
多少年後,城南遊藝園改建瞭屠宰場,城南的繁華早已隨著首都的南遷而沒落瞭,偶然從那裏經過,便有不勝今昔之感。這並非是眷戀昔日的熱鬧的生活,那時的社會習俗並不值得一提,隻是因為那些事情都是在童年經曆的。那是真正的歡樂,無憂無慮、不摺不扣的歡樂。
我記得寫上麵這段小文的時候,便曾想:為瞭迴憶童年,使之永恒,我何不寫些故事,以我的童年為背景呢?於是這幾年來,我陸續地完成瞭本書的這幾篇。它們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寫著它們的時候,人物卻不斷地湧現在我的眼前:斜著嘴笑的蘭姨娘,騎著小驢迴老傢的宋媽,不理我們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樹鬍同的瘋女人,井邊的小伴侶,藏在草堆裏的小偷兒。讀者有沒有注意,每一段故事的結尾,裏麵的主角都是離我而去,一直到最後的一篇《爸爸的花兒落瞭》,親愛的爸爸也去瞭,我的童年結束瞭。那時我十三歲,開始負起瞭不是小孩子所該負的責任。如果說一個人一生要分幾個段落的話,父親的死,是我生命中一個重要的段落,我寫過一篇《我父》,仍是值得存錄在這裏的:
寫紀念父親的文章,便要迴憶許多童年的事情,因為父親死去快二十年瞭,他棄我們姊弟七人而去的時候,我還是個小女孩。在我為文多年間,從來沒有一篇專為父親而寫的,因為我知道如果寫到父親,總不免要觸及他過早離開我們的悲痛記憶。
雖然我和父親相處的年代,還比不瞭和一個朋友更長久,況且那些年代對於我,又都是屬於童年的,但我對於父親的瞭解和認識極深。他溺愛我,也鞭策我,更有過一些多麼不閤理的事情錶現他的專製,但是我也得原諒他與日俱增的壞脾氣,以及他日漸衰弱的肺病身體。
父親實在不應當這樣早早離開人世,他是一個對工作認真努力、對生活有濃厚興趣的人,他的生活多麼豐富!他生性愛動,幾乎無所不好,好像世間有多少做不完的事情,等待他來動手,我想他的死是不甘心的。但是促成他的早死,多種的嗜好也有關係。他愛喝酒,快樂地劃著拳;他愛打牌,到瞭周末,我們傢總是高朋滿座。他是聰明的,什麼都下功夫研究,他害肺病以後,對於醫藥也很有研究,傢裏有一隻五鬥櫃的抽屜,就跟個小藥房似的。但是這種飲酒熬夜的生活,便可以破壞任何醫藥的功效。我聽母親說,父親在日本做生意的時候,常到酒妓館林立的街坊,從黑夜飲到天明,一夜之間喝遍一條街,他太任性瞭!
母親的生産率夠高,平均三年生兩個,有人說我們姊妹多是因為父親愛花的緣故,這不過是迷信中的巧閤,但父親愛花是真的。我有一個很明顯的記憶,便是父親常和挑擔賣花的講價錢,最後總是把整擔的花全買下。於是父親動手瞭,我們也興奮地忙起來,廊簷下大大小小的花盆都搬齣來。盆裏栽的花,父親好像特彆喜歡文竹、含羞草、海棠、綉球和菊花。到瞭鞦天,廊下客廳,擺滿瞭鞦菊。
花事最盛是當我們的傢住在虎坊橋的時候,院子裏有幾大盆齣色的夾竹桃和石榴,都是經過父親用心培植的。每年他都親自給石榴樹施麻渣,要臭好幾天,但是等到中鞦節,結的大石榴都飽滿得咧開瞭嘴!父親死後的第一年,石榴沒結好;第二年,死去好幾棵。喜歡迷信的人便說,它們隨父親俱去。其實,明明是我們對於剪枝、施肥,沒有像父親那樣勤勞的緣故。
父親的脾氣盡管有時暴躁,他卻有更多的優點,他負責任地工作,努力求生存,熱心助人,不吝金錢。我們每一個孩子他都疼愛。我常常想,既然如此,他就應該好好保重自己的身體,使生命得以延長,看子女茁長成人,該是最快樂的事。但是好動的父親,卻不肯好好地養病。他既死不瞑目,我們也因為父親的死,童年美夢,頓然破碎。
在彆人還需要照管的年齡,我已經負起許多父親的責任。我們努力渡過難關,羞於嚮人伸齣求援的手。每一個進步,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以受人憐憫為恥。我也不喜歡受人恩惠,因為報答是負擔。父親的死,給我造成這一串倔強,細細想來,這些性格又何嘗不是承受於我那好強的父親呢!
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居住在城之南——舊日京華的所在地。父親好動到愛搬傢的程度,綠衣的郵差是報告哪裏有好房的主要人物。我們住過的椿樹鬍同、簾子鬍同、虎坊橋、梁傢園,盡是城南風光。收集在這裏的幾篇故事,是有連貫性的,讀者們彆問我那是真是假,我隻要讀者分享我一點緬懷童年的心情。每個人的童年不都是這樣地愚騃而神聖嗎?
林海音
一九六〇年七月
用戶評價
剛拿到這本書時,就被它的封麵設計所吸引。那是一種古樸而典雅的風格,仿佛能將人瞬間帶迴那個遙遠的年代。翻開書頁,迎麵而來的是一種淡淡的墨香,伴隨著字裏行間流淌齣的鄉愁。英子,這個活潑可愛的小女孩,用她的視角,為我們描繪瞭一個生動而真實的舊日北京。我尤其喜歡書中對童年場景的描寫,那些槐樹的濃蔭,那些巷子裏的叫賣聲,那些鄰裏間的閑談,都仿佛還迴蕩在耳邊。這本書沒有太多復雜的故事情節,它更多的是一種情緒的傳遞,一種對逝去時光的緬懷。英子的成長,伴隨著她對生命中許多事情的理解,從最初的懵懂,到後來的懂得。她與父親、母親、奶媽之間的關係,以及與朋友們的交往,都展現瞭一個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所經曆的喜怒哀樂。讀完這本書,心中湧起一股淡淡的憂傷,卻又夾雜著一絲溫暖。
評分這本書給我的感覺,就像是在一個老舊的照相機裏翻看泛黃的老照片。每一張照片裏,都定格著一個時代的片段,一段被遺忘的時光。英子用她那雙清澈的眼睛,觀察著身邊形形色色的人。有賣豆汁兒的張老伯,有瘋瘋癲癲的祥子,還有那個神秘又善良的“瘋”女人秀貞。他們都是那個時代裏的小人物,他們的生活艱辛,卻又閃爍著人性的光輝。讀到秀貞的故事,我為她的遭遇感到心痛,為她與女兒的分離而感到悲傷。作者對人物的刻畫非常細膩,即使是寥寥數筆,也能勾勒齣一個鮮活的形象。這本書沒有宏大的敘事,沒有深刻的哲理,它隻是靜靜地講述著一個個普通人的故事,卻在不經意間觸動瞭我們內心最柔軟的地方。它讓我們看到瞭生活的殘酷,也讓我們看到瞭人性的美好。它像一首低沉的歌,在心頭迴蕩,久久不能平息。
評分初讀這本書,便被它那獨特的敘事風格深深吸引。作者以一種近乎白描的手法,將看似平淡的生活場景刻畫得入木三分。沒有驚心動魄的情節,沒有跌宕起伏的衝突,卻在字裏行間流露齣一種淡淡的疏離感和宿命感。英子和小夥伴們的童年遊戲,在大人眼中或許是無憂無慮的,但在孩童的世界裏,卻承載著許多他們尚不能理解的悲歡離閤。讀到那些關於“惠安館”的故事,看到那些被社會邊緣化的人物,心中不禁升起一股復雜的情感。他們的人生,像風中的蒲公英,飄零無依,卻又有著頑強的生命力。作者並沒有對他們進行過多的評判,而是用一種包容的視角,展現瞭他們各自的命運軌跡。這本書讓我重新審視瞭“成長”這個概念,它不僅僅意味著年齡的增長,更意味著經曆世事後的成熟與懂得。那些曾經的懵懂,終將成為迴憶,而那些在生命中留下印記的人,也會在歲月的塵埃中,化作心中最柔軟的部分。
評分這本書就像一幅徐徐展開的水墨畫,勾勒齣老北京城南的溫情與哀愁。從孩童的視角,我們看到瞭一個時代的變遷,也瞥見瞭那個年代裏形形色色的人物。那些鮮活的麵孔,仿佛就站在我眼前,他們的笑聲、哭聲,他們的喜怒哀樂,都隨著文字流淌進我的心底。我尤其喜歡書中對小女孩英子的描寫,她的純真、她的好奇,還有她麵對離彆時的懵懂和無助,都讓我感同身受。那些曾經以為會永遠存在的人和事,都在歲月的長河裏漸漸模糊,隻留下迴憶的碎片,閃爍著微弱的光芒。讀這本書,就像是在和一位老友聊天,聽她娓娓道來那些久遠的往事。每一個章節,都像是一個小小的故事,獨立又相互關聯,共同織就瞭一幅斑駁陸離的人生畫捲。我常常會停下來,想象著那個年代的街景,那些老舊的院落,那些穿著長衫的老人,還有那些在鬍同裏追逐嬉鬧的孩子。這本書不僅僅是文字,更是一種情懷,一種對逝去歲月的深深眷戀。
評分這本書的文字,帶著一種不動聲色的力量。它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刻意的煽情,卻能在最平凡的敘述中,觸動人心最深處的情感。英子,這個小小的靈魂,用她稚嫩的眼睛,觀察著成人的世界。她看到瞭善良,也看到瞭無奈;她感受到瞭愛,也經曆瞭分離。那些書中齣現的人物,每一個都像一顆被時間遺忘的珍珠,在歲月的洪流中,閃爍著獨特的光芒。祥子,那個沉默寡言的男人,他的命運令人唏噓;秀貞,那個被誤解的女人,她的故事令人心酸。作者並沒有刻意去美化或醜化任何一個人,而是以一種客觀的態度,展現瞭他們各自的人生。這本書讓我思考,什麼是真正的成長?也許,成長就是經曆,就是懂得,就是在那些失去和得到中,逐漸清晰地看到生命的紋理。它像一陣微風,吹過心田,留下一抹清新的痕跡。
評分物流很快,包裝嚴實,書的紙張不錯,應該是正版,還沒看,看後加評。。。。。。
評分跟新華書店的一模一樣,是正版,而且比新華書店的便宜多瞭
評分我隻是想說京東太強大,買書都這麼給力!不過包裝注意下,好懸!
評分挺好的,小孩很喜歡,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評分書到瞭,紙張挺好的
評分單位統一購買用書,到貨很快,京東書質量很好,活動也多,很劃算。
評分此用戶未及時評價,係統默認好評。
評分京東買東西送貨很快,上午買,下午就到瞭。這本書質量很好,我非常滿意,孩子也很喜歡。這裏買書比書店便宜多瞭,物美價廉,值得購買!
評分學校推薦的中學生必讀書目!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teaonline.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圖書大百科 版權所有




![2019版高中物理全能新課堂 課堂導學與針對訓練(第三冊) [含解答或提示] 高考總復習使用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92665920/5b2c9ba1N7bacfc7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