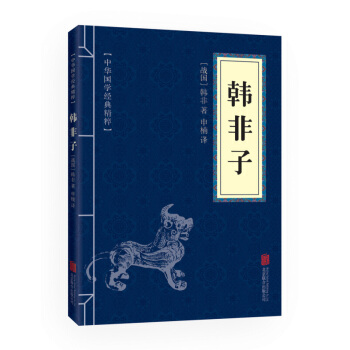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野史记》、《说史记》为杨早撰写的“新史记”系列的前两种,系列主题为“重述与改写”,以另类视角对近代历史文本作细节化的呈现。
《说史记》尽力使用小小说或小说片断的方式,采取不同的视角,从迥异于客观叙事的角度,来重新讲述近代故事,并在叙述过程中引入生活的细节;另一方面,是从小说或新闻中撷取生活细节,来展示近代社会的日常生活。
总之,这些“重述与改写”,都在于让历史与传奇,借由新的写法,活泼灵动起来,转化为当代人的叙事与阅读资源。需要强调的是,作者坚持“信而有征”的资料方式,即首先保证文章的出处,纵非信史,亦有凭借,其意义在于可以从中看出历史是如何在传说中播散与变化的,包括《野史记》副题为“传说中的近代中国”,而作者基于当代生活经验与间接文本知识的“私心揣度”的加入,是为“回到现场”提供可能的生动观照。
可以说,这个系列是对历史描述的一次有益尝试。每篇文章轻松可读,但几乎无一字、无一事无来历,背后有深厚的历史支撑。
内容简介
《说史记》为其“夕花朝拾”系列写作计划的第二种。分为“说史”、“史说”、“说记”三部分。“说史”记录稗官野史、名人轶事,用类似小小说或小说片断的形式,使用不同的叙述视角和叙事方式,重述晚清民国史上脍炙人口的传说、记事与人物经历。该辑又分为不同系列,如名妓系列、名案系列等。体例如《上进》、《名妓列传之出关》等。
“史说”撷取晚清民国史上一些有趣的碎片、细节,加以集合、串连、拼贴,夹以议论。体例如《车站故事》、《〈顺天时报〉眼中的张勋复辟》。
“说记”是从各类生活细节入手,从晚清民国小说中摘取不同的生活细节,类似一种“晚清民国的社会生活史”的片断式写法,体例如《房子的故事》、《上个世纪的时尚饮品》。
总之,本书以平民、另类的视角重新观照历史,写作思路遵循“以小见大”、“还原现场”等原则,尽可能让读者看到宏大叙述遮蔽下的历史细节,以及这些细节折射出的历史风云。
作者简介
杨早,祖籍苏北,生于川南,1995年于中山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2001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05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近年主要关注中国近现代舆论史与文化史、当代文化研究等。曾发表《京沪白话报:启蒙的两种路向》、《五四时期北大学生刊物比较》、《评价于丹:学术规范还是传播法则?》、《新世纪文学:困境与生机》等论文,著有《纸墨勾当》、《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民国了》,编有“话题”年度系列(《话题2005》至《话题2013》)、《沈从文集》、《汪曾祺集》、《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等,译著有《合肥四姊妹》。其微博、公共微信,都有几十万的粉丝数量。他经常出入媒体宣传活动,被多家出版单位邀请为年度图书评选的嘉宾,多次上电视评论节目,如《锵锵三人行》等。
精彩书评
★近年,尤其是辛亥年,关于近代史的大众写作越来越多。但编辑在做市场调研时发现,这类大众历史类写作还是多偏于通史,希望能对近代中国有一个统观式的了解。这类书其实从出版的角度讲,无论是写法还是装帧设计,模仿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的痕迹很明显。杨早对于片断掌故的经营、笔端的活泼、叙事中的特写能力,这类书都不好与之相比较。另外如《明朝那些事儿》式的游戏笔墨,在史家的层面上,杨早这样的写作又显得比较严肃或者高级了。——卫纯
目录
第一辑北里记5午后6
出关9
买笑13
义赈16
淴浴19
夜宴22
诗妓25
见夫28
闯宴30
错爱32
花榜35
规矩38
第二辑食货志41
平叛42
招商44
房价50
股灾51
史带55
上进58
学徒61
改判64
商会67
教授70
北迁72
有功75
第三辑时闻录78
190079
遮羞85
抢米87
白话97
三字99
南北101
黑血103
狱中105
首都106
复辟107
五四110
汽车112
穿越113
大王116
援外119
车站124
第四辑乙巳年126
回望127
过年129
对俄132
分省135
蹈死137
绝交139
救灾141
抵货146
募捐149
看报155
当兵158
留学161
告示164
精彩书摘
午后虽然是冬天,阳光还是很好。眼睛看上去似乎有相当的温度,真要抬腿出去,才知道风吹得脸上身上一道道地疼。连隔壁当铺的黄狗,都将头埋在腿腹间,蜷成一团,全力抵抗这该死的冷。
冬日的午后,短。陕西巷的午后,转眼似乎太阳就有些西斜。
老胡坐在云吉班的门洞里。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但他不能关门,做生意,规矩!他倒不怕冷,干冷总比南方的阴冷容易抗,只要不站在风窝里。
他把头上的毡帽压压低,左手下意识地去顺那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却逮了个空,才省觉已经是民国,辫子剪了总有一年多了。
向右横了一眼,三河县来的田妈躲在南房檐下的长凳上,手上抓着抹布,低头打盹,胸前被口水湿了一片。哼,在上海的时候,下人哪敢这等放肆?谁不是格挣挣地立着,手不停脚不歇地做事……园子里的花没浇,鹦鹉笼的水罐也空了,灶下的柴草散放着,伊倒不怕冷,在这里打瞌铳!
“田妈!……田妈!……”
田妈蓦然惊醒,慌张地东张西望,看见是老胡,一颗心才放了下来。“好!老胡,你大白天见鬼了吗?鬼叫鬼叫!”
“田妈,你看看你什么样子?乖乖,若是妈妈和小姐现在回来,你阿要炒鱿鱼?”
田妈看看天色,还早着呢,心里不服气,嘟嘟囔囔地去擦柱子:“梅香拜把子——都是底下人,充什么二爷呢?!”
老胡没有听见田妈的抱怨,他直愣愣地望着大门外,早十年的时光一层层叠在空荡的大街上。
四马路上那时节,一过了中午,打茶围的陆续上门,莺莺燕燕几多热闹,自己掂着大茶壶,跑进跑出地要果盘,添茶水,打发小三子去老正兴叫烂肉面,凑个空,跟下脚娘姨打情骂俏,摸一把她们的肥屁股……冬至到了,也摆几台酒,热烘烘的菊花火锅,亮白赛银的铜手炉……
“难不是民国害的?好好地在四马路,说南京好,去南京,张辫帅打得来,又往北逃,南京到清江浦,清江浦到天津,天津到北京……乖乖龙的咚,现时客人!毛都没一根!”他忍不住又一次的唠叨。
田妈白了他一眼。伊还记着仇,何况,老胡说的地方,伊一处都没有去过。
“也不怪北方客人势利,规矩全坏了!旧时的客人,头次上门打茶围,英洋一只,末后都是出出进进,吃吃喝喝,碰碰和,做做花头,倌人亲热得来,像做了三世夫妻!一台酒八只洋,高兴末摆摆双台,双双台,全看阿是恩客!现如今,一台酒涨到了廿只洋,还讲究现过现,我要是客人,我也弗高兴!”
田妈突然来了兴致,抹布一丢,挨到老胡的长凳上。
“我听说,小姐那时才十四岁?上海的印度阿三不让她出局?”伊说“出局”仿的是张妈的上海腔,歪歪扭扭的腔调,难听得来。
“工部局是有介样章程。大抵是几位阿姐带着伊,局上末总有几位客人没有相熟的倌人,顺便荐过去,要末唱几只小调,代几杯酒……不然,何必去南京讨生活?”老胡还在愤愤然着南京。
“我还听说,小姐的老太爷还是在旗的呢,是杭州做官的!真不?”见老胡今天少有的耐心,田妈斗胆捧出久亘胸中的疑团。
“是倒是的,”老胡倒没有怪田妈嘴多,“伊是姨太太生的,老太爷一死,就被大娘赶出来,不几年娘就死了,张家姆妈,就是伊的奶妈带着伊,在浙江抚台家中帮忙,倒出落得读过几天书……好景不长,浙江‘光复’,哼哼,”老胡鼻子里很不屑地哼了光复两下,“张家姆妈带伊逃到了上海,过不下去,才将伊押到班里来的。”
田妈对这段掌故很满意,咂了咂嘴:“咱们这位小姐,刚来的时候,说是上海的红倌人,我瞧长相呀……不是说不好,比云庆班那几位呢……”
老胡不乐意了,瞪大了眼睛喝道:“田妈,弗要瞎三话四!阿拉小姐在上海,在南京,哪里不是局票多得接不完?大清的时候,不像民国的人,眼睛只看得见一张面孔!小姐知书识礼,又会自己写写歌词,才气多得溢出来,满地都是!你来这里半年,上门的哪个不是达官贵人,公子哥儿?哪个不说小姐是才女?”
田妈被他一吼,不敢再说,搭讪着要走开。眼前一暗,一部包车停在门口。
下来这两个人,不凡!都穿着军呢的大衣,獭绒的呢帽。尤其右边这个人,戴一副盲公镜,慢慢走下车来,走上台阶,走进门洞。摘下镜来,容长脸儿,两只眼微微斜着,有神。
没带随从,老胡却直觉这是贵客,不由得立了起来:“两位先生,您是?”
左边的来客脸上带出了诧异:“怎么?不可以打茶围?”听着是翘舌头的北边人。
老胡高了兴,又紧跟着把歉意往脸上挂:“您先生还是南边规矩,而今民国了,北边儿客人下午不会来,掌灯时分才有生意。小姐、妈妈今天去东岳庙烧香去了,要不,您去哪儿转转再……”老胡撇着京腔,跟田妈的上海话一样别扭。
右边那位“哦”了一声。低头想想,抬头对老胡说:“我是慕名而来,特为见见你家小姐。既是不凑巧,晚上没空,我留一张片子吧。改日再来。”他说话也有口音,似乎有点儿湖南,又有点儿云贵一带。
老胡点头哈腰,从那位手里接过了片子,又帮他们叫住没走多远的洋车,一直候着车出了街口,才慢慢欠身回到门洞里,见田妈正在涎着脸看,不禁得意地道:“看着没有?慕阿拉小姐的名来的!看那一身的行头,起码是个统领!”
他眯起眼,借着倾斜的阳光看片子上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
“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昭、威、将、军、全、国、经、界、会、督、办、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参、政、院、参、政、蔡、……蔡什么?认不得。田妈,你……算了,你又不识字!”
那是“鍔”字。
出关
望平街与别处不同,它的日夜是分为四段的。
白天大部分的时候,这里人影寥寥;日落向晚,渐渐有记者、编辑回报馆,也许在路边吃一碗烂肉面,而闲散了一天的各商铺、茶楼的伙计们,此时各各精神起来,预备迎接诸位老主顾。
入夜时分,国际新闻版、各地新闻版已经基本上排好,京里的命令和要闻,或许有些还在路上,至于那些跑巡捕房的伙计,多半要回馆交代一下,再回捕房去盯个通宵。茶楼酒馆里灯火通明,喝茶的,吃宵夜的,磨时间的,全上海跑新闻的大小角色大约都会露露面,交换交换情报。此时的望平街,无数消息在空气飘荡,碰撞,起伏,融合,在雨前茶和虾仁炒面的气味里从一张嘴到另一张嘴,它们竞相奔跑,看谁能爬上当天的版面。
此时的望平街,才不枉叫做“中国的舰队街”,大英帝国的新闻中枢,也未必比这里热闹。
凌晨两点之后,报馆人员渐次散去。全上海的报贩砉然拥进望平街,争抢各馆新出的日报。人头涌涌的望平街,好象闸北的小菜场。
在我看来,半夜那一段远比此时迷人,有一种激动人心的气息。
民国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晚上十一点,我正坐在青莲阁茶楼临窗的位置里看报。老余匆匆走进来,将一卷电报纸掼在茶桌上。
“京里的可靠消息,蔡松坡出京了!”
团团圈圈桌上的同行都被吸了过来,老余一下子变成了总经理级别的人物,有人搬椅子,有人掺茶,有人点烟,有人帮着叫“烂肉面一碗,油水足点”!
更多的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大发议论:
“蔡松坡是任公的学生,前一阵他竟然头一个签名赞成帝制,我早就觉得不对劲了!”
“可不是。《群强报》报道说松坡将军日日云吉班,夜夜小凤仙,醇酒妇人,纵情声色,如今看来,大约是韬晦之计,以消极峰的疑虑。”
“哈,老胡,就叫老袁好了,什么极峰、总统,咱们在租界里,不鸟他!”
“松坡听说为了小凤仙和夫人起争……”
“先别吵!老余,你说说,松坡是怎么出的京?”
所有眼光都集中在老余的瘦脸上。
老余两手一摊:“我也不知道!电报上只说,老头子今天才收到松坡的告假书,其实他大概昨天就失踪啦!”
一时很静默。往往有头条新闻而无详细内容时,便是各报记者编故事的好时机。
一年眨眼就过去了。这一年里,商家的招牌和帐簿换上了有“洪宪元年”字样的,未及两月就又得换回民国。大伙儿叫苦不迭。还是青莲阁的老板有远见,说:“不换!”老袁的手虽长,却也伸不到上海公共租界来。
是十一月十一日吧,我们凑在青莲阁,品评北京公祭松坡大会的挽联、电报。大家最措意的,当然是蔡将军那位红粉知己的两付挽联。
“听说小凤仙自己也去了,穿蓝布大褂,见到的人说,相貌不过中等,语带南音,颇有英气。”
“这副长对据说出自易哭庵之手,‘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患余生,萍水相逢成一梦;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好则好矣,轻巧了些。”
“哭庵嘛,哪里合适凝重沉稳的路子?有人说短联也是他的大作,我看不像!”
“着哇,有人说就是小凤仙的亲笔,那便可称得上才女喽!”
“不错,‘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简明,贴切,有出处,将来必成名联!”
唏嘘感叹声中,有人问了一句:“到底去年松坡是如何出的京?”
是呀,蔡锷蔡松坡是怎么出的京?在松坡仙逝、小凤仙失踪之后,这成了我唯一能够追索的谜题。
京沪报纸上有几种说法。一种是,松坡与朋友在长安酒楼痛饮,召小凤仙侑酒,席间蔡忽称自己“腹痛”,借尿遁出了酒楼,直奔前门车站,乘夜车往天津;
另一种是松坡与小凤仙乘车出游,故意在京城内绕来绕去,将跟踪特务绕晕了之后,两人经过东车站,梁启超已经派家人在彼相候,蔡遂登车东行,小凤仙一人回班。
还有一种,说是留日士官生的学长、兴中会老会员哈汉章(时在陆军部任职),借用老母八十大寿的机会,掩护蔡松坡逃走,却将此事栽到了与松坡出双入对的小凤仙身上。小凤仙被迫停业回南,但老袁随后也侦知是哈汉章的把戏,还没来得及收拾他,帝制已经无望,哈逃过一劫。
这几种说法腾传人口,都有人信,但都不能让我全信。以老袁对松坡的疑忌,蔡出走前数日,他还指引军警执法处处长雷震春搜查蔡锷住处,对蔡本人,应当看守更加紧密才是。即使被蔡溜走,也应立即发现,大肆搜捕,岂能容松坡轻轻松松到达津门?
这个疑团萦绕我心头多年。四十年后,偶然遇见许姬传先生,他告诉我,小凤仙后来嫁到东北,偶有机缘,晤谈梅兰芳梅老板,语及前事,他也在座。
“哦?她自家怎么说?”我自然又惊又喜。
许先生说,小凤仙自称当日(11月18日)是云吉班班主寿辰,贺客众多,蔡松坡趁机在小凤仙房里摆酒相贺,并特意撤去窗纱,卷上纸帘,让外面看见屋内情形。冬日严寒,蔡将大衣、皮帽挂在衣架上,怀表摆在桌上,只穿单衣到院里如厕。院子里厨师、跑堂、贺客、大茶壶,全是人,松坡趁着乱劲溜出门外,叫了辆洋车。想那八大胡同离前门能有多远?不一时到了车站,梁任公早派老家人曹福买了两张三等票等在那里,于是松坡随曹福上车离京,经天津转日本,回了云南……
“等等,”我刚释然的疑云又聚成了堆,“蔡松坡离开云吉班后的事,小凤仙是怎么知道的?”
“她不知道,她也是后来看报上说的。”
我听老余说过,老袁在帝制前后,极其关注国内局势与反袁诸人动向,前门车站、天津梁任公寓,都有特务日夜监视。蔡松坡离开云吉班的说法是可信的,部署也很周密,但后面的情节就太简单了。
没想到这么多年后还能重逢老余!两人还像当年在望平街一样,手挽手去喝老酒。下酒菜除了松花皮蛋茴香豆,也少不了蔡松坡与小凤仙。
“你这个疑问我能解释,”老余的瘦脸笑成一朵花,“洪宪事后,我就被派到了北京当跑腿员,曾经看到北京报纸上有一条札记。作者我也认识,叫侯疑始,是严复严几道的弟子,和朝野都有极深的关系。
“那条札记上说,蔡松坡不但在云吉班布下了空城计,而且,他还从那里打了个电话,就是打给总统府,他说,有要事要面禀总统,问何时可以谒见。那边讲,下午两点。电话打得很大声,守在外面的特务都听见了。所以蔡松坡出云吉班,是大摇大摆出去的,还要把门的人给他雇常用的汽车哩!特务们既知他是去总统府,又未携行李,当然以为他去去就回。
谁知蔡松坡坐汽车路过前门车站,突然下车,一去不回。司机当然以为他乘车逃逸,马上报告。执法处立即命车站特务登车巡检,但怎么都找不到与松坡形状相似之人,天津的特务也在车站守了一天一夜,连根蔡松坡的毛都没有见着。
蔡松坡哪儿去了?他在车站雇了辆人力车,直奔一个朋友家,就在那儿剃须易容,扮成一个运煤的工人,担着空筐,满脸煤黑,天擦黑时出了东便门,雇骡车奔通县。在通县小店里住了两天,等风声松了,才由通州间道赶到天津,见梁任公,定下了反袁护国的大计。”
老余一口气说完。我都听傻了。
听说小凤仙病逝于1976年,离蔡松坡因喉癌死于日本,整整六十春秋。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是一本让我感到“惊喜”的书,它的结构和叙述方式,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本以为会是一本传统的历史读物,没想到《说史记》却以一种非常“接地气”的方式展开。作者仿佛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说书人,用生动、幽默,甚至带点俏皮的语言,将那些沉重的历史事件娓娓道来。他擅长运用类比,将复杂的历史概念,用我们熟悉的现代生活场景来解释,瞬间就拉近了历史与读者的距离。更让我惊喜的是,作者在叙述中,常常会插入一些富有洞察力的个人观点,但这些观点并非武断的批判,而是基于对史料的深入分析,是一种引人深思的启发。我能够感受到作者并非只是在“说”历史,更是在“思考”历史,并在思考中,注入了自己的灵魂。这种非线性、多角度的叙述方式,让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兴趣,就像在听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充满了未知与期待。
评分《说史记》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它对历史的“温度”。很多历史书,读起来总觉得隔着一层冰冷的面纱,那些人物和事件,都像是展柜里的陈列品,缺乏生命力。《说史记》则不同,它用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笔触,去触碰历史的脉搏,去感受那些人物的喜怒哀乐。我能够想象到,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一定是对那些历史人物倾注了极大的情感,去理解他们的困境,去体会他们的挣扎,去欣赏他们的闪光点。这种“情”的注入,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数据,而是有血有肉的故事,是关于人性的深刻探讨。我读这本书,不是在记忆枯燥的年代和人物,而是在体验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感受着那些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渺小与伟大。这种“温度”的存在,让我在阅读中,能够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仿佛自己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部分。
评分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像许多历史著作那样,总是聚焦于宏大的叙事,或是冰冷的数据。相反,《说史记》像是穿梭在历史的肌理之间,捕捉那些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细节,用一种近乎考古的耐心,去发掘那些被遗忘的情感和微小的事件。《说史记》没有给我一种“知识轰炸”的感觉,反而像是在一块古老的丝绸上,慢慢地用指尖描摹出那些精美的纹路。我能感受到作者在研究时,那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对史料的审慎考量,以及最难得的,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他能够从一段看似无关紧要的记载中,勾勒出人物的心理活动,从一幅模糊的壁画中,推测出当时的社会风貌。这种“见微知著”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我不再是那个被动接受信息的读者,而是仿佛参与了一场历史的解谜游戏,跟着作者一起,抽丝剥茧,最终拼凑出那个时代的真实图景。这种阅读体验,既是一种智力的挑战,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让我对历史有了更立体、更鲜活的认识。
评分这本书就像一位老友,在某个午后,轻轻地翻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读《说史记》的过程,并非是那种紧张刺激的侦探小说,也不是那种需要绞尽脑汁去理解的哲学著作。相反,它更像是一场温润的对话,一位博学而亲切的长者,用他那饱经风霜的眼睛,透过历史的烟尘,为我细细道来那些曾经鲜活过的生命,那些跌宕起伏的时代。我仿佛能感受到作者并非只是在陈述事实,更是在品味,在感悟。他对历史人物的描绘,充满了人性的关怀,无论是叱咤风云的帝王,还是默默无闻的百姓,在他笔下,都拥有了鲜活的血肉和真实的悲欢离合。那种历史的厚重感,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扑面而来的气息,让我沉醉其中,久久不能自拔。那些看似遥远的往事,在他的叙述下,变得触手可及,让我不禁思考,在那些相似的境遇中,如果是我,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这种代入感,是这本书最迷人的地方,它没有高高在上说教,而是以一种平等而尊重的姿态,邀请我一同走进历史的纵深,去感受,去理解,去回味。
评分这本书最让我欣赏的一点,是它对于“提问”的尊重。很多历史书,倾向于给出结论,而《说史记》则更像是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平台。作者在叙述过程中,常常会抛出一些令人回味的问题,这些问题并非是为了刁难读者,而是为了引导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去探究历史背后的逻辑和动因。我能够感受到,作者并非满足于简单的“知其然”,更渴望“知其所以然”。他鼓励读者主动参与到历史的解读中来,去辨析不同的观点,去形成自己的判断。这种互动性的阅读体验,让我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积极地参与到历史的学习中。我仿佛看到,作者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是在指挥,而是在邀请,邀请我一同去探索,去发现,去理解那些复杂而迷人的历史真相。这种引导性的叙述,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也让我对历史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
评分很有意思上老冯的奇人异事有一拼
评分非常好看的书。很有趣味性。赶上活动,划算。赞一个。
评分书不错,慢慢看
评分正史与野史并存,互为参考,互为印证。
评分看惯了正事,在看野史便觉妙趣横生
评分一个个小故事,方便阅读
评分一直对京东的购物体验很满意
评分包装不错不错的,还没看,先备着。
评分很喜欢 买回来开卷有益呢 推荐哦…………………………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eaonline.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大百科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