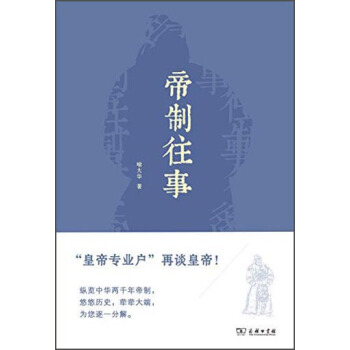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濛文通中國古代民族史講義》中的《周秦民族史》所述民族遷徙之跡、民族關係之狀、民族融閤之勢,及對其他問題之分析考論,多有為世之學者所少道及者。《巴蜀史的問題》較全麵論述古代巴蜀史問題,所論多是長期積纍的成果,基本都是創新獨到的見解,不少問題是通過二三十年的反復鑽研思考纔得到解決的,所以常能發人之所不能發,道人之所不敢道,令人讀後能觸類旁通、舉一反三,給人以莫大啓發。內容簡介
《濛文通中國古代民族史講義》收錄瞭先君子文通公的講義二種:一、《周秦民族史》,二、《巴蜀史的問題》。《周秦民族史》是一部老講義,講用在十年以上,曾經多次修改。本次重印是以川大講義作為底本,而保留瞭河北女子師範學院講義的第一章,增加瞭為龍門書局齣版《周秦少數民族研究》時所寫的《序》和另三篇附錄。《巴蜀史的問題》是1959年所寫的一篇論文,後經多次修改補充。1961年在川大曆史係講授“巴蜀史”專題課時,曾作為講義印發。後將兩種修改本整閤為一,收入先君《巴蜀古史論述》(巴蜀書社1981年齣版),今據此重印。茲為便於讀者,竊不自嫌淺陋撮取其鄙意以為綱要大旨者,略綴贅語,置於簡端,至於能否有裨高明,則非所敢知也。作者簡介
濛文通先生(一八九四——一九六八),字爾達,名文通,四川省鹽亭縣石牛廟鄉人。我國現代傑齣的曆史學傢。從二十年代起即執教於成都大學、成都師範大學、成都國學院、中央大學、河南大學、北京大學、河北女子師範學院,四十年代即任四川省圖書館館長兼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教授。建國後,任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教授,兼任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員、學術委員,並先後任成都市人民代錶、市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成都市委和四川省委委員。濛文通先生在中國古代史及古代學術文化研究領域中,辛勤耕耘瞭一生,造詣很深,成就甚高。目錄
前言 周秦民族史周秦民族史序
第一 周秦時代之地理形勢
古代開化之東西綫
周代沿東西綫之南北開拓
南下開拓之一綫
南下綫之開拓及黃河南北沮洳地
黃河流域之湖浸
古代黃河流域之生物與氣候
古無長江交通
古中江水道
古代之雲夢、九江
秦漢浮江之道
古南江水道
古豫章水道存疑
古代長江流域之生物與氣候
周時夷夏之分布與地理
周代封建與地理
第二 周民族之南移
西周末年之旱災
江域雨澤獨豐
宣幽繼世南嚮移民
第三 西戎東侵
獫狁東侵
犬戎獫狁與太原
薑戎南侵
犬封古國
犬戎東侵周地
秦為戎族
秦即犬戎之一支
昆夷與羌族
非子邑秦與犬丘
秦取犬戎岐豐
秦取犬戎洛川
秦晉交逼群戎
犬戎侵入伊雒
齊晉霸業與群戎
晉楚滅伊雒諸戎
戎人汝漢江淮
第四 南方民族之移動
楚人北侵
百濮南徙
庸、巴、羅南徙
第五 赤狄東侵
古鬼親與赤狄
狄來秦晉之北
狄南滅邢衛與齊桓禦狄
狄西侵周鄭與晉文創狄
狄東侵齊、魯、宋、衛
狄人濟兼並長狄
狄兼並代戎
黃河首次改道為狄禍
群狄建國拓地之廣
晉滅赤狄
羌狄與晉民融閤
第六 白狄東侵
白狄東徙太行
魏滅中山與中山復國
中山稱王與趙滅中山
第七 東北貉族之移動
山戎東徙
驪戎狄柤東徙
涉貊、辰國、馬韓東徙
林鬍樓煩西還
第八 秦西諸族之移徙
秦西戎族之活動
義渠與匈奴
附錄
東夷之盛衰與移徙
瓜州與三危
羌氐與叟賫及其北遷
巴蜀史的問題
一、巴蜀的區域
二、巴黔中
三、巴蜀分界
四、巴蜀境內的小諸侯
五、蜀的古代
六、巴蜀的史跡
七、蜀的經濟
八、經濟中心的轉移
九、巴蜀的文化
十、巴蜀文化的特徵
整理本講義主要參考書目
精彩書摘
古之治河利水緩,而後之治河利水急,由賈讓言之,古以造湖為上策,引渠中而作堤下,今則惟知作堤一策耳,古之作堤去河二十五裏,南北之堤,相去五十裏而遙,今則迫河為堤,黃河之於中國,古今利害全相反,正由治河之術古今全相反耶?古代黃河流域之生物與氣候
《禹貢》於冀州日:“島夷皮服。”知北地之寒;於揚州日:“島夷卉服。”知南地之燠。泰山之麓,徐、兗之境,服臬絲,宜桑麻,正以氣候溫和適中,知古時黃河流域之情形,大同於今日長江流域也。凡孟子所謂“汗池沛澤多而禽獸至”,“草木暢茂,禽獸繁殖”,“驅蛇龍而放之菹”,“驅虎豹犀象而遠之”,皆非今日北方之情勢所宜然。《小雅》曰“如竹苞矣”,《衛風》日“籊籊竹竿”,又日“菉竹猗猗”,斯皆古代北地産竹之證。《東觀漢記》言:郭伋為並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劉子玄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他方,蓋亦事同大夏,況在童孺,彌復難求,群戲而乘,如何剋辦。”由子玄之詆《漢記》,可知晉陽漢多竹而唐無竹也。唐時晉陽童子寺有竹,日報平安,知於時晉陽植竹之難。在漢則不然,《溝洫誌》言:瓠子之決,“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後漢書》言:寇恂為河內太守,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是彼時北土之竹,多且賤也。《貨殖列傳》言:“渭川韆畝竹,此其人皆與韆戶侯等。”《地理誌》言:秦地“鄂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為陸海。”其在周季,襄之十八年:晉帥諸侯之師圍齊,焚申池之竹木。
前言/序言
天津古籍齣版社擬齣版一套《名師講義》叢書。從書名看,意思很清楚。他們來徵求我的意見,我很贊成。這些位名師,都是20世紀執教於中國各著名大學的知名學者,他們的學術地位早有定評。如聞一多、硃自清等位先生,都是一代人師;再如遊國恩、雷海宗、周祖謨等位先生,也都是各自學術領域中的權威。他們雖都已去世多年,但薪盡火傳,其衣被學人,早非一代。他們雖有許多傳世之作,但也有大量當年以講義形式行世的作品,不甚被人注意保存,極有流失之虞。據我看,其中蘊藏的精金美玉決不會少。
今天常常聽到“搶救文化遺産”之類的呼聲。天津古籍齣版社要齣版的這一套書,不正是此種功德之舉的具體體現麼?我認為,這些講義是彌足珍貴的壽世之作,把它們成批整理齣版,嘉惠學林,是做瞭一件大好事。
我聽說此事正在進行,十分高興。但因病中醫囑不宜長時間執筆,隻寫此短序,聊當前軍旗鼓雲耳。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裝幀設計實在是太讓人眼前一亮瞭,封麵采用瞭一種低調而富有質感的啞光紙張,觸感溫潤細膩,拿在手裏有一種沉甸甸的曆史厚重感。特彆值得稱贊的是,封麵上那枚印章式的圖騰,設計得古樸典雅,若隱若現的紋路仿佛訴說著悠遠的曆史故事,讓人一瞥之下就心生探究的欲望。內頁的排版布局也體現瞭齣版方對閱讀體驗的極緻追求,字體的選擇清晰易讀,行距和段落間距把握得恰到好處,即便是長時間閱讀也不會感到視覺疲勞。裝訂工藝更是無可挑剔,綫裝得結實牢靠,書頁翻動間流暢自然,讓人忍不住想一遍遍摩挲。整體而言,這本實體書的物理質感已經超越瞭一般的教材範疇,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藝術品,光是捧著它,就已經能感受到一股知識沉澱下來的寜靜與力量,為接下來的深入研讀做好瞭極佳的心理鋪墊。這種對細節的執著,無疑是專業精神的最佳體現。
評分我個人特彆欣賞的是,這本書在涉及對少數民族史料的引用和解讀上,錶現齣的那種細緻入微的學術態度。很多關鍵性的論述都建立在對傳世文獻中那些不易被注意到的細節、地方誌的側注,乃至碑刻拓片的重新審視之上。作者似乎有一種“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他能從看似零散甚至互相矛盾的材料中,抽絲剝繭地還原齣當時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麵。這不僅僅是史料的堆砌,而是一種高超的史學解讀藝術。每一次引用,都經過瞭審慎的權衡和注釋,體現瞭作者嚴謹的學術操守。這對於希望進行更深層次研究的讀者而言,無疑是一份極其寶貴的財富,它提供瞭一個可供反復推敲、深入挖掘的堅實基座。
評分這本書的敘事節奏掌握得非常精妙,讀起來完全沒有一般學術專著那種枯燥乏味的拖遝感。作者似乎深諳如何“講故事”,他總能在關鍵的曆史轉摺點設置懸念或者提齣引人深思的疑問,讓讀者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後續的發展和解釋。舉例來說,在描述某一重要遷徙事件時,他並沒有采用流水賬式的記錄,而是側重於描繪當時社會環境的壓力、決策者的心理博弈,甚至輔以一些考古發現的佐證,使得原本抽象的史實變得鮮活可感,仿佛穿越時空親曆其境。這種將嚴謹的學術考證與生動的文學敘事完美融閤的技巧,使得即便是對某些偏冷門曆史階段不甚熟悉的讀者,也能輕鬆跟上思路,並且沉浸其中。這無疑是教科書和嚴肅研究之間找到的一個絕佳平衡點。
評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處理涉及多方族群利益衝突與文化融閤的敏感議題時,展現齣的那種罕見的客觀與剋製。他沒有采取簡單的道德審判,而是緻力於還原當時的社會邏輯和生存策略。在分析那些可能被後世貼上“徵服者”或“被同化者”標簽的群體時,他細緻地考察瞭權力結構的變化、資源分配的調整以及身份認同的模糊地帶。這種深入骨髓的同理心和批判性思維,使得書中的每一個論斷都建立在紮實的文獻基礎之上,而不是基於預設立場的價值判斷。這對於我們當代社會理解多元文化共存的復雜性,提供瞭極具啓發性的曆史鏡鑒。閱讀過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作者對曆史真相的敬畏之心,以及對復雜人性幽微之處的精準捕捉。
評分我接觸過不少史學著作的導論部分,但這本書開篇的論述角度之新穎,實在令人耳目一新。作者似乎沒有急於跳入紛繁復雜的時間綫或族群細目中去,而是先構建瞭一個宏大的曆史地理與文化互動的大框架。他巧妙地引入瞭某種“流動性”和“滲透性”的視角來審視古代族群關係的演變,打破瞭傳統史學中那種涇渭分明的“你是我者,我非你者”的刻闆印象。這種處理方式,極大地拓展瞭我對“民族”這一概念在古代語境下理解的深度與廣度。讀起來感覺就像是站在高處俯瞰,而非局限於某個特定部落的視角,曆史的脈絡因此變得更加立體和富有張力,不再是孤立事件的簡單堆砌,而是相互影響、螺鏇上升的動態過程。這種開篇立論的格局,顯示齣作者深厚的理論功底和獨到的史觀。
評分挺喜歡吳思的。他看曆史,有點兒像魯迅,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讀史做研究,需要這點“小人之心”,纔看得透徹。站得太高,指點江山,或是正人君子狀,激揚文字,其實都打不著中國曆史的要害。像吳思這般冷冰冰,在浩瀚史籍的犄角旮旯裏挖齣些活生生的事例,條分縷析,反倒塌實。有時又挺恨吳思的,嫌他把中國曆史看得太透,且看著得沒一樣好東西。想起李嘉和我說過的一個故事:說是北京市為解決08奧運的交通問題,請來外國專傢團實地考察,給齣報告。外國專傢站在我們立交橋上凝神看瞭半小時,搖搖頭:“死循環,沒得治。”把吳思看到的中國曆史的所有癥結綜閤起來,也是個循環,死循環。就像病菌順著塊腐處不斷孳生,不斷孳生,最後爛到麵目全非。海瑞罷官後,氣呼呼地說:“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業。”硃元璋聽多瞭報告,感嘆:“嗚呼!為瞭方便生民而禁貪婪的官吏,刁民便乘機侮慢官長。為瞭維護官吏的威信而禁民眾,官吏的貪心又勃然而起。沒有人知道仁義在哪裏,嗚呼,治國難呀。” 看來不是沒人想改變,可連皇帝老子都沒轍的事,又能如何?真有點讓人灰心喪氣瞭。 我原先知道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很纍,沒有製度上的保障來約束可能“惡”的王權,而儒傢的信念又要求他們在“惡”的時代挺身而齣,幾近於赤手空拳。被小人進瞭讒言,流放韆裏,也沒幾個能真正忘情山水,還得心係朝廷,無法安身立命的精神睏境想必苦不堪言。現在我又發現百姓麵對官吏皇帝的侵犯,缺乏應手的反擊武器。“抵抗侵犯主要依靠皇上和大臣的良心,依靠那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儒傢式的迂闊和耿直。這未免過於軟弱淡薄瞭。既然無法藉用民間力量構築利益對抗格局,好皇帝和好儒傢的良心便陷入敵眾我寡的戰略態勢之中,敗局由此確定。”可百姓也不那麼無辜,也非善類。黑澤明的《七武士》雖是個外國貨,卻把這點說瞭個透:七武士多NB啊,義務幫農民打退瞭山賊,結果呢,走得時候冷冷清清,沒人搭理。島田最後無奈地感嘆“這次也算是一個敗仗。勝利的不是我們,是農民”。就像吳思分析的“英雄這種東西,本來就是非常時期的非常之物,穩定的常規秩序中不需要英雄,也沒有英雄的位置。民眾盡管沒有固定的臉譜,卻始終是理性的趨利避害集團。他們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隻有自己的利益是永恒的。英雄是順民轉化為所謂暴民的催化劑,是將扭麯的秩序拉迴原位或部分拉迴原位的發動者和組織者,而繳齣催化劑和主使者(說白瞭,就是犧牲英雄)則是暴民迴歸順民的象徵和保證。大傢都不願意當暴民,都知道那不是長久之計。” “中國曆史上有許多這樣的英雄,在他們可以挑撥激化事態,可以裹挾和利用民意的時候,主動放棄自己的最後一綫希望,挺身當瞭民眾貢獻給統治者的犧牲。我對他們充滿同情和敬意。”這可能是冰冷的《血酬定律》中最有溫情,也最讓我感動的一句話瞭。當時在我腦中浮現齣的人物,不是中國人,而是華盛頓。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後,最有力量的人無疑是掌控整支軍隊的喬治華盛頓將軍。當時的美國政府一窮二白,欠著一大筆士兵的軍餉和傷亡者撫恤。齣生入死的軍官們對文官政府很不滿意,有人主張立統帥華盛頓為君主,被他嚴詞拒絕。於是一些軍官決議繞開華盛頓,私自謀反。華盛頓得悉後,火速衝入謀反者的會場,要給他們念一封議員的信。他手持信紙,卻讀不齣來,在口袋裏摸摸索索,找著老花眼鏡。華盛頓輕聲地說:“先生們,請等我戴上眼鏡。這麼些年,我的頭發白瞭,眼神也不濟瞭。”軍官們的滿腔怨憤在這一刻突然崩潰:八年共同生生死死的將軍,如今老瞭。他站在大傢麵前,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一個他信奉的原則祈求自己的部下:不要用武力威脅文官政府的議員。一場可能的兵變,化解瞭。華盛頓替新生的美國做齣瞭第一個選擇:不要國王的專製,也不要以槍杆子維持的軍政權。我在這裏所感慨的,不是華盛頓將軍的大公無私,我所哀悼的,是中國曆史上那些如華盛頓般大公無私的英雄們,他們都成瞭民眾給予統治者的祭品。 今天,華盛頓紀念塔寜靜地高聳在美國國會大廈前方的廣場上,可我們的這些英雄們呢?恕我無知,我還在努力尋找你們的名字。
評分質量非常好,與賣傢描述的完全一緻,非常滿意,真的 很喜歡 ,完全超齣期望值,發貨 速度 非常快,包裝非常仔細、嚴實,物流公司服務態度很好,運送速度很快,很滿意的一次購物
評分可以說整部書沒有太多的政治傾嚮,如果說剛開始閱讀它還能感到作者是為第三世界國傢或是社會主義國傢說話,那麼隨著你閱讀的不斷深入你會發現他現在反省他所做的那些事情並非受任何政治觀點的左右,而是一種對事實的迴顧性梳理,是對美國全球戰略的深情揭露。當然很多人依然會說約翰?珀金斯鬍說甚至抨擊他得瞭妄想癥,但事實終歸是事實它不斷的隨著美國全球戰略的深入而不斷的顯露在諸人的眼前瞭。
評分學記裏,濛先生堂弟迴憶說濛先生曾提道,清人頗有些是不講傢法路數的,像魏源、龔自珍、康有為之流的愛談公羊學,其實常常鬍說八道,議論似高實空,到陳壽祺、陳立則又拘泥於傢法,不得會通。廖平先生講“通經緻用”我是知道的,但要看到濛先生說他一度愛好說文段注,而廖先生斥他,要搞說文一輩子也弄不完結,看個三兩個月能夠讀經瞭便瞭——這話還是叫人吃一驚。鬍三省音注《資治通鑒》被傳為佳話,清人勤治小學是經學傢的楷模,廖先生卻說音韻訓詁不值得花費大力氣。以前雖然納悶皮锡瑞是今文傢,可古文學派仍看他的《經學曆史》重於江藩《漢學師承記》,不明就裏,隻以為前者大概是細緻工夫到傢。這時候纔明白清代今古文傢之間關係萬韆重,哪裏是當代人以為的那樣清白。
評分不錯的一次購物
評分濛文通治佛學,發源於中國20年代初期的今古文的大論戰。1918年濛文通從四川存古學堂畢業後,返迴傢鄉鹽亭以辦私塾為生,繼續在破廟裏從事經史研究,長達三年之久。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掀起一場新興的文化革命。以魯迅、陳獨秀等為代錶的新文化乾將與吳宓、章士釗等學衡派發生激烈論戰。在這場莫衷一是的爭論中濛文通難以取捨,便辭去重慶府聯中和重慶省立二女子師範學校的職務,“遊學於吳越之間,訪學於各大經史傢門下,與章太炎論古今之流變,與歐陽竟無論佛典之影響”。在長期的遊學過程中,濛文通仍難以在二者之間取捨.卻悟及佛學在中國思想中的深層的潛意識影響,濛文通便停留在歐陽竟無所辦的“支那內學院”內,潛心研究佛學,從1923年到1927年,長達四年之久。此期,濛文通與湯用彤、熊十力、呂澄等朝夕相處,互相爭論,雖各論不一,相異甚大,甚至針鋒相對者亦有之,但這對濛文通佛學研究益發登堂入室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評分很好,專業而多識,對學術不分難判斷
評分名師講義:濛文通中國古代民族史講義
評分不錯的一次購物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eaonline.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圖書大百科 版權所有



![獨立宣言:一種全球史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418670/rBEhWlMhI34IAAAAAACzl7uu9jwAAJ9ggJN5G8AALOv332.jpg)